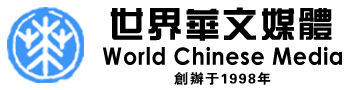李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李端
陕西人民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邀我写点东西,我慨然应允。因为在1983年至1988年那五年多的编辑经历,在我看来,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既令人神往,又令人怀念。
真的。
一
1983年7月,我从西北政法学院(现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因为新盖的八层办公大楼已经在刷漆装电梯,就不须到大院东南的平房编辑部去加座了,可以直接上楼,等待全部人马搬上来即可会合。
这样,我有幸成为第一个在新盖的办公大楼里整个六层“捷足先登”的办公者。
因为开始是一个人坐在宽敞明亮的硕大房间里,所以每天早晨我打开办公室的大门,第一个动作,常常是先要站在东边的窗台前,望着东方,一会儿发呆,一会儿伸胳膊,阳光灿烂,街市如瀍,想这想那,有种飘飘欲飞的侠客感。
果然,这是一个阳光般明媚的群体,也有着很多阳光般的人,以及记忆深刻的阳光日子。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时期。整个出版社,到我们这一届,可以说集中了当时七七、七八和七九级“新三届”的大部分“新鲜血液”。加上毕业不几年的工农兵学员,差不多有三十多人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把不同学校的新鲜空气带到社里,介绍新文章,购买内部书,辩论新概念,探讨新观念,谈恋爱,搞郊游,争煤气灶,打康乐棋,感觉似乎又回到学校一般。
更为可爱的是,这里的领导老中青结构合理,编辑部的生活丰富多彩,总有新鲜的异样感觉。
记得时任副总编兼部主任叫南岗,江苏盐城人,新四军老记者,身体特棒,成天乐呵呵,但只要他笑着说“还不坏”,大家一乐,就知道这是最高评价了。副主任陈戈,天津人,是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地下党女大学生,看似严肃却开口幽默,别人笑,她装着不笑,特好玩。而室主任杨永奎,则是一位讲究实用之学的政法校友,常常是看着我们这一班青年人玩得过久,也只是半庄半谐地站在一旁,笑笑,又笑笑,大家就知趣地跑开了事。在这样开明的领导之下,其他人即使不是青年,其实也都是年轻人了。
记忆最深的,当然是打康乐棋了。每天上午,十点一过,号称是“工间操”的康乐棋,就马上热了起来。这种玩具,现在似乎已经绝迹,但当时,其实就是用象棋棋子打的花式台球,再加上保龄球的功能,很有竞争性。恰巧,这台康乐棋就在我们办公室,所以,每天在康乐棋台上发生的所有趣事都会成为一天里心情敞亮的不竭话题,而每一个人在棋场上的各种表现,最能表现整个楼层各个年龄段编辑们的个性特征。
七七级经济编辑室的曾宣传,是最热心者之一,打棋时先要把眼镜卸下来,用手擦擦,然后举全身之力一杆直戳,哪怕出界,也要以势大力沉取胜;新分配来的山东大学研究生沈光云,则总是带着鸭舌帽扎根香烟慢慢瞄准,一杆下去,不论中靶与否,先用陕北话说一声“手气不行”,就尴尬地转圈圈了;与我同级从西北大学毕业的文史编辑室贺治波,干练潇洒,先蹲下来,用两只大眼睛平着棋盘左看看,右瞄瞄,正在慨叹棋位不好,突然就一杆子出手,然后就是不服的笑,特神气;而1970年从西北农学院毕业的经济室主任朱玉,则更有一番转悠择机的功夫,任你再催,绝不急躁,用杆子反复丈量后,再屏息敛气,才准确出杆,并立即进行点评。他后来成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可能就与这种严谨的作风有关系吧?总之是,除了我这个干什么事情都太过随意者以外,像山西大学毕业的竹守章,四川大学毕业的张海潮,西北大学毕业的王敏,以及后来从各校分配的马来、李俊宏、朱小平、李晓峰等几位毕业生,都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不服,也各有各的精彩。
其实,康乐棋就是一种象征。它表明这是一个开放年代的开明单位,社会上各种时兴的话题和选题,都像开心的康乐棋一样,令我们关切关注,充满想象,如阳光般向往。
二
编辑部,当然要以编辑好书为要事。现在想起来,也是阳光满满,一片暖色。
记得我到出版社之后,自己组织的第一本书稿,就是曹锡仁老师的《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这部书稿的写法很新颖,尤其是语言风格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思路宏阔而别出机枢,带有很大的创新性。但在时任主管副总编刘夏至先生的配合编改后,此书甫一出版,就获得当年陕西省大学生书市金奖,并随后获得全国北方十五省区社科图书一等奖。尤其是,由陕西师范大学刘明琪和西安石油大学卢宏定两位年轻教师撰写的针对《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一书的书评,竟获得《博览群书》杂志社举办的“全国书评大赛”一等奖的第一名,一时风头无两。《西安日报》甚至在报道中称其为“书界之冠”——老实说,我当年离开陕西,到中国特区时报应聘,大约就是凭着这本书的那几个红本本光彩,而在第一轮就被选中,并当场聘为“科教文版”主编的,从中亦可见当年的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文化影响力。
而在编辑部,我们也会接到一些书稿,通过我们的编辑加工而增色的。记得当年仍在团陕西省委《陕西青年》杂志社工作的陈四长先生(后调入出版社,成为我的领导),曾送来一些书信体手稿,开始名叫《给青年男女的++封书信》,我编辑时起名为《婚恋夜笺》,并加以点评,深得作者和市场好评;还有陕西省司法厅劳改处的张宏轩,送来一堆问答类资料,初名叫做《劳改知识问答》,我后来经过编辑,改名为《劳改内参》,后来也获得全国北方十五省市区社科图书二等奖,甚至完全出乎作者的预料而得到提拔;还有一本书,也是省工商局个体处送来的知识问答之类书稿,我们后来改为《个体工商户案头必备》,出版后竟自行扩印了十几万册,几乎做到全省一家一本,蔚为大观。
现在想起来,当年在出版社那种宽松自由环境下,轻狂如我的起书名功夫,可能为我后来在《深圳商报》做总编室主任时,常常被戏称为“标题大王”而积累的自信吧。
三
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89年之前,是我从20多岁到30多岁的青春时期。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刚毕业的大学生,其实就是在出版社大院开始婚恋成家的。
与那个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一样,我们的内心始终都沐浴在一片光明的浪漫期许中。
1986年8月,我女儿刚出生不到三个月,听说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天津举办一个高级编辑研修班,经过争取,我得到了时任出版社领导的恩许,获得了进修半年的机会。那个时候,我爱人还要上班,但我就是认准要多学点东西。结果,不仅担任进修班级临时党支部书记完成学业,还在学习期间,在《出版工作》和《编辑学刊》发表了四五篇文章,就出版文化发表了不少不知天高地厚的观点,甚至与国内出版大腕刘叶秋先生对战,由此可见少年轻狂的时代代入感。不仅如此,就是在此期间,我还完成了我的第一本著作《成才与第二文化环境》,并且是由当时的文化名家高尔泰为我作序,还被《文摘报》转载。此书后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获得全国大学生“金三角图书奖”,似亦可见那个时候,真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春痴狂。
其实,那种青春气象,不只是我。在整个出版社,发表作品,甚至著书立说的大有人在。而各个出版社和编辑部之间的鲜亮选题,也一个接着一个在酝酿推出。问题是,当我后来到了专门成立的青年部后,却似乎感到有些迷茫。尤其是,分管我们的副总编刘夏至先生逝世后,记得我和兰州大学新分来的张孔民十分悲戚,甚至非常落寞。我们在出版社大楼里,贴出由张孔民撰文、由我用毛笔书写的《哭老刘》长文,似乎是一种无奈的预感。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起,我们那一群年轻人长大了,成熟了,开始为评职称、争获奖和分配房子等问题闹心了。出版社的阳光依旧,人更多了,新分出的更多出版社也都各有所忙。我们的青春可能要过去了。
虽然后来我力图以到特区的转换形式减缓青春的远去,但毕竟时代的太阳已经升至中天,别有情趣。
30年过去,南方的阳光虽然更热,但我的青春光热,似乎只停留在出版社那几年的生涯,并始终与阳光同在记忆的深处。

在北京与出版社老同志王志钧等华夏出版社同仁座谈

1987年出版社工会组织去秦岭旅游

1988年,青年部去西安鲸鱼沟春游

1989年,青年编辑部春游

1989年春,青年读物编辑部集体骑车春游
作者简介

李端,笔名端木公,男,陕西合阳人,1955年生。1983年自西北政法学院哲学专业毕业来社,先后在政治理论编辑部和青年编辑部任编辑。1988年底到南方,先后任《特区时报》编委,深圳记者站站长;《深圳商报》经济新闻部、总编室主任;广告部,发行部总经理及报业集团读者俱乐部主任。2000年后,任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会长兼秘书长。先后出版《成才与第二文化环境》《中华百年报刊大系》《敬业时代》《梦非梦》等著作。现居深圳,为“端木公工作室”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