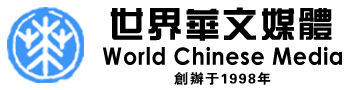周利群:作为世界公民的印度人
周利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旅居欧洲的时候,经常遇到发色与肤色比较深、高鼻深目、操着传说中咖喱味儿英语的人,多半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古代的时候,这个地区还不叫南亚,也没有一分为八的民族国家,统一称作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他们的主体民族称为印度斯坦人,主要使用语言为印地语、乌尔都语这类印度斯坦语。在南亚次大陆之外,他们被称为海外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 and person of Indian origin,NRI-PIO),虽然不住在本土,仍然具有强烈的向心力和很高的辨识度
2017年秋季电影《维多利亚与阿卜杜勒》的巨幅广告遍布伦敦街头,英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王维多利亚头上的王冠和阿卜杜勒包的头巾特别吸引眼球。在现代叙事中,这位印度哥们不再被称为“红头阿三”,而是女王的心腹(Closest Confidant)。昔日印度的开发是在日不落帝国对于的殖民活动中逐步完成的,如今印度的铁路交通系统、政治法律框架、医疗保障体系、现代建筑艺术等等都是英殖民时期的遗产。物产丰富的印度也让东印度公司放弃了探索的初衷,贡献了英女王王冠上最璀璨夺目的宝石。历史上英帝国在全球的殖民活动,也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语言现象“女王英语”(Queen’s English)。印度、马来西亚等地区,生活中使用本地语言,官方文书和正式活动中全部使用英语,属于全球英语传播链中的拓展圈,英语熟练程度仅次于欧美母语者。印度人的英语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不是一般的强,众多国际文学奖的印裔作家群体可以印证这个观点。

电影《维多利亚与阿卜杜勒》
当我见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八十多岁高龄仍然思维敏捷头脑清晰,我想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之前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诗圣泰戈尔呢。当我了解到美国硅谷三巨头中谷歌和微软的CEO都由印裔来担任时,我也不以为意,印度人擅长数学与计算机嘛,很正常。当我听说伦敦现任市长是一位巴基斯坦人时,有点不淡定了;外来移民想成为英国的下议院议员(Member of Parliament,MP)就很不容易了,更何况是伦敦的市长。历久弥新的文明,在现代世界中产生一两个商界精英或大学者并不难,但移民到英国如此保守的国家,融入其政治体系并成为佼佼者着实不容易。
出差巴黎,跟出租车的印裔司机谈到伦敦市长的事,他表示理解,能出现这样的印裔市长是因为移民的基数大,移民与当地社区的融合程度高,当然也少不了他个人的努力。同时他提到,欧洲大陆的车是左舵,英联邦国家的车是右舵;南亚移民根本不需要适应交通规则和驾驶习惯就可以在英联邦国家开车,故而去这些地区当司机更容易。蓦然理解了为什么旅居的剑桥最大出租车公司PantherTaxi有那么多司机都是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地区来,也理解了街上的南亚超市,印度餐馆。
提起英国的印度菜,有人说甚至比印度的印度餐馆平均水平还要高。亲测过的剑桥印餐,无论是北印的馕和坦都里烤肉,南印的多萨和咖喱鱼,以及人气饮料芒果奶昔(MangoLassi),都跟在印度吃到的菜肴味道无差,相对来说卫生水平更高。剑桥的食堂,无论是学院还是大学的,即使只有三道主菜,必定有一个是素食。不知道这个习惯什么时候开始,或许是从二战后英国所有的村子里都配备印餐外卖那时候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超市里买到的非西餐便当中,印餐的口味也远比中餐好吃,简单的咖喱羊肉饭也像模像样。
对于移民群体来说,语言和饮食问题解决后,才有余力考虑上层建筑的问题,比如协会,比如社区,比如宗教。2017年在巴西里约开国际会议的时候,恰逢学会领导层改选。选举前,两位中国候选人在副主席一职上跃跃欲试,争拉选票。选举后,所有参与投票的中国人都垂头丧气,说这两位候选人为了一个职位分掉了票数,最后结果是投票的中国人那么多,却没有推上去任何一位。而两位参选的印度人则不一样,其中的一位上演讲台后坦白说只是来热闹一下请大家支持另外一位印度候选人,最后集中了票数使另一位印度候选人成功入选主席团成员。在协会及其他组织中,印度人的抱团儿也被称为有效团结,帮助了一位又一位的印度人在国际组织中获得理想的席位。
海外印度人不仅仅“拉帮结派”,还“拖家带口”。迪拜棕榈岛海边散步的人群中,拖家带口的南亚人熙熙攘攘,冒着高温在街头兴高采烈地观摩世界最奢华的酒店。在巴黎17区的公园里,看到说着印度语言的一家子,回收垃圾桶的塑料瓶,淡定地谋生。有一些在美国IT行业工作的印度中年人,自己站稳脚跟后,把父母从印度接过去养老。担心父母亲无法融入美国的生活,又开发了印度裔为主的楼盘供他们居住生活。在这样的社区中,大部分人说印度语言,信奉印度本土的那些宗教,每天做祭祀或者礼拜,过着与印度本土居民几乎一模一样的生活。
餐馆瑞士伯尔尼宗教博物馆,发现其中五种宗教之一的印度教庙由南印度人建造,斯里兰卡人经营。湿婆、毗湿奴、林伽、大蛇等雕像浓绘重彩,五颜六色令人炫目。高耸的凯拉什山,被众多的神祇簇拥着,迫人生出一种巍峨憧憬之情。熏人的印度香料,使整个大厅都弥漫在一种情境中。朗朗神曲,绵绵不绝地播放,让步入神庙的人进入印度调频。门口出售的粉丝米饭油炸蔬菜,是颇具特色的斯里兰卡口味,让我这个访学过印度的人也生出一丝怀念。与同馆的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场所相比,印度教庙竟是相对热闹的,因为印度人毕竟是每天都会做祭祀的。
之前一位社会学背景的华裔教授提到,前些年伦敦某东亚商场很快倒闭,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经营不善,社区的规模受到蚕食,拿到的土地也不得不归还政府。与之相反,印度人的社区不断在壮大,因为印度人一直在建设庙宇,仅一个社区中前后造了十八个印度庙。信仰宗教自由的英国政府,只能支持印度人社区的壮大。分析下来,海外华人想要扩大自己社区,应该向印度人学习,不断建设宗教场所。这个分析有戏谑的意味,没有相应宗教信仰盲目建设庙宇,不知道是否具有竹篮打水的性质。
我想,海外印度人与当地社会的兼容,应该不仅仅是用庙宇占领了地产。而是他们有效团结,让精英不断上行,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为自己的族裔发声。同时他们尽可能参与当地社区的活动,与当地人的生活紧密连接。对于携带到海外的老幼妇孺,他们创造了印度的社区,印度的家庭,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塑造牢固的民族认同。
前两天问一个朋友家混血儿子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卓不凡”。直接表达出卓尔不凡的理想,我猜是印度爸爸的直率,而不是中国妈妈的含蓄。中国人谦逊久了,或许可以学一学印度人的果敢及其他长处,以便于更快地成为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融入国际社会。
来源:人类学微刊2019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