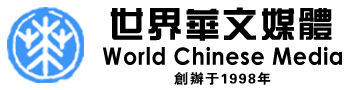韩少功:下海闯海南,退休回湖南
韩少功/口述 张英/采访整理
改革开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体制内,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时代,开始重新设计人生下半场。
在大时代下,这些“文化人”的个人命运发生了怎样的转折?作者张英在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文化观潮”系列口述。讲述“文化人”所经历的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发的是作家韩少功的口述,讲述他下海闯海南办《海南纪实》《天涯》的经历及退休后回湖南的生活状态。

韩少功近照
在中国的作家里,韩少功是个少见的行动主义者。他本是长沙城里人,年轻时下乡做知青当农民。
1988年,35岁的韩少功离开长沙,携家带口,和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大军的一员。他放弃了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常委的仕途,放弃了湖南作协稳定、安逸的工作,确立刚刚成立连办公室都没有的海南作协。
2001年,韩少功辞去省作协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的职务,回到湖南,在插队的汨罗县偏远山区,依山傍水而居,过起了养鸡种田的生活。
他奔波在湖南和海南之间,天气暖和的日子,呆在湖南乡下,浇水种菜,天气寒冷就回海南,读书写作。
和我住在同一个小区里的作家蒋子丹感叹说,“我认识韩少功差不多40年,亲眼见证了他从小韩变成了如今的老韩。他的人生修改过程,是我目力所及的人群中,很少有人能达到的成功过程。”
蒋子丹认为,韩少功的成功,不是官职高低,多大名气,赚了多少钱,而是韩少功活得纯粹,坚持理想,不忘初心,活得安稳,人生有定力,精神世界一直是热血青年,没有被外在世界改变。
“就回湖南下乡盖房子这件事,我不知道听多少作家朋友兴致大发地宣讲过,但真去农村盖了房子去过日子的人很少,而且没虚度这些日子的人,更绝无仅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以流水般的刚毅和柔韧,朝着预定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行,最后抵达自己的人生目标,不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少功不成功,谁人可称成功?”
2016年7月,作者对韩少功进行了一次深度采访,讲述他的人生过往。
跨越过海闯海南
1988年,我离开长沙,一家三口,女儿那个时候才8岁,去了刚刚成立的海南。
我和老婆、丫头,带着被褥、脸盆、热水瓶,乘上从长沙到湛江的火车。其实那个时候,老婆连工作都没有,还没有找到接受单位。大年初三那天,我们坐船到了海口秀英港码头。我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我喜欢海南。之前,我们参加《钟山》杂志组织的笔会,第一次来到了海南岛,就被这里蓝天白云大海所吸引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我对海南的印象:海南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大陆中原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暗处。
尽管那时候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的道路,连一个像样的交通标志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引诱着我。我回长沙不久,听说海南特区即将成立,将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我就心动了,便鼓动叶蔚林等朋友一起前来创业。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我29岁的时候,就因为文学创作的成绩,先后当选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常委,也是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第三梯队”接班人选。如果留在长沙,按部就班,再等几年,前途会很光明。
而当时的海南,一穷二白,刚刚建省,人多工作机会少。没有工业和轻工业的基础,旅游业没有起来,唯一的经济产业就是农业。我把工作关系落在了海南作协筹备组,但当时机构没有编制,办公室只有8平米,还是借的省文联的,一家人暂时借住在姐姐家。
合伙办《海南纪实》
我带到海南的积蓄,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
当时,正值文学低谷,文学杂志稿费低,图书发行量也少。为了谋生,我和几个湖南去的朋友,找了一个刊号,办了一份杂志《海南纪实》。开始,我们想要创办一份名叫《真实中国》的杂志,但最后被管理部门定名为《海南纪实》。
我们当时野心很大。在我们的规划里,《海南纪实》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出版社、函授大学、报纸等等,在申报《海南纪实》杂志社的同时,他们还申报了一家出版社,一家函授学院。只是出版社最终没有获得批准。
办杂志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我和张新奇、林岗、蒋子丹等几个朋友一起弄的。当时编辑部是租的,在海府路的省干休所内,就一间小房子,两张办公桌。
此前,我在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杂志当过四年的编辑。办杂志,也算是熟门熟路。根据市场调研的结果,我们把《海南纪实》杂志的办刊方向定为新闻刊物,主打新闻时事和纪实文学。
办杂志,热点稿是“大菜”,还有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观察解析,加上几个页码的彩色新闻图片,很快,凭着内部的样刊,在全国书刊批发市场跑了一圈,第一期杂志印刷了60万册,在期刊市场上一炮而红。
《海南纪实》一成立就是公司化,股份化运作,几个员工,责权分明,待遇和个人劳动付出挂钩。高劳动付出和高收入挂钩,点燃了杂志员工的热情,杂志发行人员像打了鸡血,在全国各地出差推销杂志。
我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并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
我们的第四条规定:“杂志社蔑视和坚决革除旧式‘大锅饭’的寄生性,所有成员必须辞去原有公职,或留职停薪,或将公薪全部上交杂志社,参加风险共担的集体承包,以利振奋精神专心致志,保证事业的成功。除特殊情况经主编同意外,任何人不为其他单位兼任实职。”
很快,我们的杂志就成为畅销期刊。那时候,人民币还没有50元和100元的,最高面额是10元,发行工作人员用大麻袋装钱。我们没拿国家一分钱,在一年时间里为国家赚了几百万利税和固定资产。
当时我们去税务局交税,当地税务局说从未从报刊征过税,不知如何办。我怕风险,让我们的财会参照当时的标准,交了几十万税款。杂志发行量破百万赚钱后,因为利益分配,也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
1989年,才办了一年的《海南纪实》,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的缘故,最终停刊。
我当时有点沮丧,但也不悲伤,就回家写小说去了。办杂志也累,花时间很多,压力也很大。
我回到了作协,当专业作家,写了一些散文,就是《夜行者梦语》《心想》《完美的假定》《南方的自由》《海念》《为什么还要写作》等文章,在小说之外,开辟了一条道路。
当主席办《天涯》
1995年,我在家里写《马桥词典》,即将修改完成。
那一年,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蔚林届满退休,主管负责人找我几番谈话,让我接任主席。我不想当官。做行政管理不是我兴趣所在,也没这种才华。拖了一年多,上级领导找我谈几次,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才接手。
当时,海南作协一穷二白,就十几个人。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中,办一份好杂志是最有意义的项目,其他的工作都应该为这个实体服务,否则作协几乎没有存在的意义。
当时全国的文学类杂志很多,省、地、县都有文学杂志,普遍情况不太好,除了几本好杂志发行量好一点,其它的杂志发行量就是一万以下,无法维持基本生存,基本上靠国家养着,半死不活的。
当时《天涯》没有影响,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我们当时查了一下账,每期大概也就一两千份,而且大部分是关在仓库里。面对这种困境,杂志怎么死里求生,只能改版。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是文史哲,不分家。《史记》是历史也是文学,《孟子》是文学也是哲学。英文里的“writer”,指的写作人,不光是作家。我们要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把《天涯》办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
我们也突破“作家”固有概念,凡是写作的人都是“作家”。这样,我们就发现“作家”,其实不是指所谓的纯文学,其实是包含了所有拿笔写作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很多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慢慢地成为了我们的作者。
我们把一些学者和作家放到一起,就诞生了“作家立场”这个栏目。我们希望展示作家真实的思想和真知灼见,不管是随笔杂文,专访对话、会议纪要,只要有品有料就行。
另外,我们把一些来自社会上普通人的写作,他们日常的文体,比方书信、日记,放到一起,就有了“民间语文”这个栏目,文学并不是文人的事情,老百姓生活里日记、书信、便条,同样是文学宝贵的一部分。再加上小说、散文、诗歌,注重文学与思想的结合,《天涯》成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
1995年底,改版后的第一期《天涯》上市。这一期,有方方、史铁生、叶兆言、叶舒宪、孙瑜、昆德拉、张承志、李皖、华孚、苏童、何志云、陈思和、杭之、钟鸣、南帆、格非、韩东、蒋子龙、薛忆沩、戴锦华等人的作品集体亮相,社会上的反响还不错。
《天涯》杂志改版第一期的征订单声明:“《天涯》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
《天涯》之所以引发知识界的关注,就在于杂志的面貌和定位。海南是很偏远的一个角落,但你的眼光要盯向全国,乃至全球。你关注的问题,是脚踏实地,是全社会普遍感受到的问题,就会找到感兴趣的那部分读者。
那时候的作协,不是什么参照公务员的管理,是一个面目很模糊的机构,是企业还是社团,还是事业单位,模糊不清。我们当时在体制上也做了一些改进,每个季度,做一次内部的民主考评,无记名互相打分,根据得分多少,与每个人奖金、级别晋升挂钩,让大家把工作做好。
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办《天涯》的,从租房子,到筹集杂志的印刷经费,到全国去跑发行渠道,找邮局,跑民营书店代销杂志,利用到各地开会的机会,去书店和代销地收账。什么都靠自己,一针一线、一砖一瓦地做,杂志就是这样慢慢做出来的。
《天涯》改版两年,就成为全国著名杂志,在读书界赢得了“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奠定了自身在中国人文知识界的地位,在国外的影响也渐渐荡漾开来。
退休回湖南种菜
人年纪大了,就越活越简单,越来越安静,不喜欢热闹喧嚣的场所。
2000年,我辞去海南省作协主席和《天涯》杂志社社长职务,和妻子一起,回到当年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插队的湖南汨罗农村。读书、写作、种菜,一年的大多数时间,在那里一直住到现在。
我是长沙人,父母都是职工,城市人。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作为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地方在湖南汨罗天井茶场,距离我现在住的地方,有20公里。
我现在记得当时的插队生活:每天一大早,大喇叭一喊,就要早起集合,和农民一起去黄土地里干活,除了中午吃饭时间外,上午下午都在干活,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每天都是疲惫不堪,坐着都能入睡。
到农村生活,有些人不一定合适。农村生活条件还是蛮苛刻,比如家里有老人或自己要经常去医院看病,不方便;如果要有孩子上学,也不合适。我搬到汨罗的时候,孩子已经读大学,独立了,也没有老人需要照顾。
我家坐落在一处三面环水的水库边。房子是两层小楼,上上下下七八间房,一个大凉台。花了两千块钱买了一片荒地,自己找当地农村施工队盖房,入乡随俗,盖成与农民老房子,红砖墙、黑瓦、木头门窗。屋里的家具,都原生态的,树皮没有刨去。
院子里搭起了架子,还种了杨梅树、橘树,也有黄瓜。读书写作累了,就穿上胶鞋,开荒种地,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自己去当地学校公共厕所的粪池,挑粪浇水施肥。蔬菜长虫了,戴上老花镜,用手捉虫子,然后养鸡、喂鸭。
我现在半年在湖南乡下,半年在海口家里。我在乡下也上网、打电话、读报纸,和外界联系。每天早上6点左右起床,喂猫,喂鸡,把这些吵着要吃的家伙侍候好。白天遇到干旱或渍涝,就得常常挑着粪桶泼菜,施肥。有时地上没有太多的事,或者天下雨没法上地,我就可以整整一天,在家读书写作。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上富裕了,生产工具、生活水准、交通条件等各个方面,都比以前好太多了。当然,也有问题:当年的乡村社会结构也趋于解体,青年人大都出外打工,村里缺乏活力,乡村文化处于凋敝中。
最先几年,住在乡下,地方又偏僻,也担心安全。当地有几个小混混,整天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便警告说,别人家你们去得,但韩嗲(村里人称韩少功为韩嗲)家你们绝对不准去。我这里就非常安宁了。
有些贫困镇,就应该去想办法帮帮忙。比如我们那里有几个村的基本设施不行,很多地方都不通路。这十多年,我想了很多办法帮他们找扶贫单位,把基本建设搞好,当时农民就很高兴。
村民们经常来我家串门。他们聊天的时候,不管什么神神鬼鬼的事,都会说给我听。张家说有一种辣椒特别好,问你要不要苗。李家会问你海南什么样,国外怎么样。王家闺女要考大学了,问你哪个大学好,或者问能不能开个后门……
开始大家都不认识,但一来二去就熟了。我老婆对种菜、养鸡、栽花弄草什么都非常有兴趣,夏天也下水游泳,八景水库的水好得不得了。当地农民问我,为啥这么喜欢游泳,我回答,在城里游泳价格贵,水质堪忧,水库游泳又不花钱,游一次就赚一次,感觉好得不得了。
除了水库里的水质好以外,我们生活用水更好,从对面山上引下来的山泉水,清凉甘甜,城里的水简直没法比。我们在这里种菜、种树、养鸡,旱了要抗旱,涝了要排涝,经常忙不过来。
农村的经济发展快,现在很多农民开私家车,农村的人也不会营养不足,都是发胖、糖尿病、脂肪肝等以前富人营养过剩带来的病。我看到的另一个问题,世道人心,道德沦丧,当然这个问题不光是乡村,城市也有,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
住在农村,要耐得住寂寞。长沙一位书商到我家来过后,被山水风情迷住,在我旁边盖了一个房子,花了将近100万元,但前后只住了60天,书商的老婆实在忍受不了乡村的简单生活,卖了房子举家逃离农村,回长沙去了。
提前退休,无官一身轻
2011年2月,我卸任海南省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两职,57岁那年提前退休,无官一身轻。
我开始当海南省文联主席是名誉性的职务,不用管实事,后来兼党组书记就很实职。我就想,要为这个单位做几件事,其实都是硬件设施建设,比如房子问题、位置问题、票子问题,我叫它们“五子登科”的事情。
三年以后,几件事情都做完了,我再干就是混了,就跟省委提出要走了。他们说你还没到退休年龄。我说我已经当了十年,按照你们规矩连续两届也够了,最重要的是我能干的都做完了,再做就是混官了,不要害我。他们也开通,尊重我的意见,所以我57岁就退下了。
我现在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之前睡觉,就像一个乡下人一样。读书、上网、写作,串门聊天。在乡下,我写出了《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记》《日夜书》等众多小说和散文随笔。
《修改过程》是我最新的作品,也是给大学同学们的礼物,是一本写给同学们、同时代人看的小说。这本小说最早源于当年湖南师范大学读书时同学们的建议。我的同学们老鼓励我,写写我们大学的同学,20年前我也写过,甚至写过8万字,后来觉得不行,就把它废掉了。
年纪大了,没有了家务和工作的困扰,人到了耳顺之年,大学班级的同学会,开得格外勤,班级同学聚会也多了。好多人几十年不见,都很珍惜彼此见面的机会。短短几天里,就把同学们这几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人生的变化都了解了。
77届大学生的人生轨迹,暗合了新中国与时俱进的巨变,一起相伴相随走下来,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生历程里的跌宕起伏、酸甜苦辣,全部都经历了。这些是我经验中的一块,丢掉有点可惜。
我现在年纪大了,经常回忆往事,《修改过程》是以几个人物的故事,来写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变迁,表现历史的嬗变和人们的真切感受。作为社会人的角色扮演者,到我们这个时候是谢幕的时候了。
回想一下,我们这代人,除了个别掌握重要权力外,纷纷退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间,退回到儿孙满堂或者是独自面对的孤独寂寞,包括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到了做总结的时候。
我的《日夜书》和《修改过程》写的就是这代人陆续退场阶段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青春期经历了“文革”、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又幸运地上了大学。毕业工作以后,赶上了出国留学、打工移民,体制改革社会巨变,国有铁饭碗被打破,有人下海经商成巨富,有人官场春风得意,有人下岗吃低保。
从没有书读到知识大爆炸,从点油灯写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从粮票、布票、肉票吃不饱肚子,从物质匮乏到丰盛过剩,自己要管父母养老送终,自己的孩子却大多数都散落天涯,逢年过节才能见面。
人到了60岁以后,对世界、家国、人生的看法可能会有反思,检讨。原来非常庄严、神圣的事物,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原来微不足道的不起眼的人和事,现在可能觉得有意义、有趣味。原来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评价,现在可能真觉得无所谓了。
我在乡下住了快二十年,我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和当地几公里村落里的老人、儿童都认识了。当地政府会请我给村干部讲课,当地的小学初中请我去讲写作,这些年,我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周围的村庄搭桥修路。
这些年,城市化发展很快,农村的改革停滞不前,年轻人和中青年骨干劳动力都进入了城市,只剩下年纪大的老人和还在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读书的孩子。中国69%的人口和90%以上的土地还在农村,他们的未来会不会变得更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运动”能否解决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我关心的现实问题。
农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偏低,种地收入太低,导致农村人才流失,而且年轻人不愿意回农村,这是农村现在最大问题。归根到底,乡村振兴需要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来源:澎湃新闻 | 韩少功/口述 张英/采访整理 2019年0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