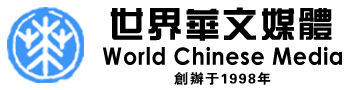序童宁创作及翻译剧本集《歌唱吧!中国》
黄纪苏
将近十年前,有回在朝阳文化馆开会,议论电影《色戒》。大家高谈阔论完了,有人提醒:还一位女士没说呢。这位女士发言的时间比推诿的时间还短点儿,而且声音微弱,没听清说什么,只记得有人说这是童道明先生的女儿。

童先生是我们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专精俄罗斯文学的前辈学者,同时也是位活跃的戏剧评论家,常在有关话剧的讨论会上见到他。老先生江浙口音,轻声慢语,最爱说“一九三某年,清华的曹禺同学……”那纯正的书卷气给会议平添一种淡远的意绪,就好比各种时空你来我往的剧场里缓缓降下一道纱幕。
童宁也学俄语,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这简直就是其父在水中的倒影。听童宁说,她在翻译俄罗斯戏剧,在写作自己的剧本,感觉春花秋雨,理应如此。不过,读了她的剧本,还真觉得有些意外。

《歌唱吧,中国》写“人民音乐家”聂耳孕育《义勇军进行曲》的那段人生。我看的时候就想:她干嘛要写他呢?童宁和聂耳之间相隔着的不是一般的岁月,而是一场沧海桑田。《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国歌,但作曲的聂耳却无缘走进国门,而是亭亭玉立在那场革命的碑林中。作词的田汉有幸走进国门,他以及许多人日后的不幸,又都化作长长的叹息,将纪念碑风蚀得面目不清。经历了20世纪那番轮回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聂耳所奔赴所歌唱的天地普遍心生幻灭。载歌载舞的当然有,但有多少源自本心就不是我目力所能及了。我能看见的是,好些歌者舞者的附近,要么有演出公司举着海报催着,要么有宣传部门攥着专款等着。而这出戏的周边显然没这些。我跟童宁打听过创作动机,她说了一些诸如沈林博士的影响还有我的戏等等,但都不如一件事板上钉钉。她说《歌唱吧,中国》其实是为她儿子写的,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如果把亲儿子比作未来储蓄罐的话,哪位家长会故意往这个罐里存假币呢?
聂耳所歌唱的天地有正面经验,也有负面教训。作为21世纪戏剧舞台上的一次回望,《歌唱吧,中国》只呈现了东方欲晓的一世,却未折射出西风残照的二世,属于简单肯定而非否定之否定,这当然是不足或缺憾。但这部戏毕竟是写给一张白纸的儿子们的,而不是写给一肚子兴衰的史家们的,求真并非第一考虑,向善才是。中国革命的正面遗产,被提纯为理想人格的营养液,继承了下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以一种家常的方式,前接后续、连为一体。

《工厂女工》写“低端”劳动者的家庭生活。我看了也觉诧异:以童宁的书香身世、学院生涯,居然能对另一个阶层的眉眼口吻、声色气味做挺生动的描画,就好像她不是童老先生的女公子,而是大杂院里“柱儿他媳妇”似的。听童宁说,是一大场病把她扔到了学术殿堂的边缘,从此跟大婶大叔只一墙之隔,因而逐渐亲近了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我一直觉得知识分子终日、终年、终生围着“开题”、“结题”、Keynote发言、五分钟回应的石磨公转,其实比蒙了眼的毛驴还悲惨。有机会上个山、下个乡什么的,究竟算“放逐”还是“拯救”,还真不能太绝对了。人的一生从小写到大写,其实就是个体熟悉古今中外各种角色、体会四面八方各样人生、把自己的脚穿到别人鞋里、把别人的梦想变为自己的追求那样一个过程。那里面,读书是捷径也是激素,不能过分依赖,知行要平衡、要相长。“知”取代“行”的结果,没准儿还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呢。即便仅仅从职业角度着眼,从事社科人文的朋友也别太把书房当回事儿了,社会人生才是真正伟大的课堂。
这个集子除了童宁创作的两个剧本,还收入了她翻译的两个剧本——文学翻译的确比其他翻译更接近“再创作”。痛苦而高尚的俄罗斯文学,早已内化进了从20后到60后无数中国读书人的三观以及审美趣味。不失根本而又容纳众流,这是小小寰球上各地人民生活的本相和常道。
所以,我更愿意把这部书看作一个心性培养和成长的故事。
2017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