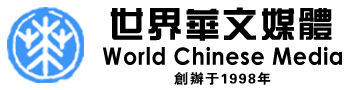中国大陆文学期刊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景
宗仁发(《作家》杂志主编)
一、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期刊的存在状态
目前,在中国大陆共有各类公开发行的刊物八千多种,社科类刊物近四千种,其中 文学刊物有几百种。这 些文学刊物的主办单位主要是国家和各省的作家协会、文联、文艺类出版社等文化机构。
从生存方式方面看,靠自身订户和零售可以维持生计的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据我所知像《收获》、《当代》、《十月》这类的老牌刊物或创刊时机遇好的刊物可以有十万八万的发行量,其余三分之二的刊物就没那么幸运了,大多发行量在几千册,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册。能够赚钱的刊物中选刊类日子相对好过,如《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这些选刊发行量大的达二十几万册,少的也有七八万册。那些无法靠发行维持生计的文学刊物其生存方式是混合型的,即有一部分政府财政延续下来的拨款,但这不足以解决全部经费需要,还要靠杂志社自己想办法去找钱,去找联办的单位或协办单位,或者建立理事会一类的后援机构,前者是找一大家来支持,后者是化整为零。如上海的几家刊物是由市委宣传部出面协调,让上海的《劳动报》与《上海文学》联办,《新民晚报》与《萌芽》联办,所谓联办,其实就是政府给的经费不足部分由联办单位补齐。贵州的《山花》与黄果树烟草集团联办,社长陈迅即是原黄果树集团的老总,《钟山》与徐州卷烟厂联办,其社长也由烟厂的老总挂名。这些联办的企业一般每年固定出资几十万元给刊物。一下子找不到一个大靠山的文学刊物,只好四处奔走多找一些企业 ,一家少出一点钱,凑起来有个十几万元。像《北京文学》、《作家》就属于这种状况。
面对严峻的生存压力一些刊物只好停刊,如广西的《漓江》,停刊后改办成一个旅游类的期刊。有的进行转向,如山西《黄河》由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双月刊改成一个专发随笔的刊物。还有的改成综合性文化类刊物,如《萌芽》、《春风》等。
代表着中国大陆文学期刊走向的几家刊物近几年也有较大改变,新闻媒体称之为“改版”。所谓改版是指在不改变原办刊宗旨的前提下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的起因是为了扩大发行量、增加读者。尽管办刊物是给读者看的,是一条最基本的道理,但真正成为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主办人一条恪守的原则还刚刚萌芽。因为在过去办刊物是不必考虑读者的,那时有无忧无虑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支撑,赔多少国家财政贴多少。
大多数文学期刊处在经济困难、人才缺乏、不良运作状态之中,这些文学期刊的处境最为难堪,一旦政府的补贴真的“断奶”,其生存就无法维持。
由于中国大陆在出版体制上采取的是一种审批制的管理办法,这意味着中国大陆的文学期刊还不是在完全式的市场经济中竞争,优胜劣汰。目前的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有限的,竞争的势态是相对易于把握的。
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期刊的转型与定位
文学期刊的转型与定位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其承载功能的重新认识。多年来在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主要是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其次就是培植作家队伍,其商品属性是被忽略不计的。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生存压力加大之后,迫使一些敏感些的文学期刊不断拓展对所承载功能的认识。办刊人已经意识到文学期刊的功能是多重的,既有精神性的,也有物质性的;既是文化的,也是经济的。这个认识的改变也是逐渐呈现出来的。一些文学期刊主办人的观念中已经初步有了经营意识、市场意识、读者意识。他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除了小心翼翼把关之外,就是不惜精力的帮助业余作者修改作品,而刊物编出来后有多少人 会看,要亏损多少钱可以不挂在心上。
今天中国大陆文学期刊的转型和定位正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到底办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刊物?
以往的文学刊物是千刊一面,都是大大小小的《人民文学》,都是“四大块”:小说、散文 、诗歌、评论。这样的办法读者不认可,市场也不接受,文学期刊的主办人也知道改是必然的。但怎么改、往哪里改,这又是没有现成药方可供使用的。于是大家就各自摸索,试图突破重围,找到一条生路。那些由于转向到文学期刊以外的类别中的刊物已游离于我们讨论的范围,这里姑且不论。仅以仍在文学范围内办刊的这些期刊为代表,由改版而显露的迹向主要是由纯文学向泛文学转化,由单调的文学刊物向杂志化的文学刊物转换。这种转化、转换起初是在一些栏目的设置上体现出来的,如《天涯》的“作家立场”、“民间语文”,《作家》的“每月话题”、“记忆.故事“,《北京文学》的”声音“,《上海文学》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这些栏目的设置其用心在于找到作家对社会生活发言的新的话语权力,提供出活生生的公众生活历史文献。翻开几家活跃的文学期刊,再也看不到“四大版块”的僵化格局,而是栏目不断翻新,丰富多彩。除了政治学、社会学成分的介入之外,音乐、美术、教育等领域的问题也被引入到文学期刊之中。《收获》今年开设的余华专栏“边走边看”,《作家》的“读房捶听”、“艺术中修辞”,《北京文学》有关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讨论等都是例证。这种文学期刊杂志化的倾向,与其说是创新,还不如说是一种复旧。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就是走的杂志化道路。那时寿命最长的由郑振铎、芽盾、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人主持或参与的《文学》月刊就是以“栏目繁多而见丰富,以专号特辑不断推出而见气势,以创作和评论之优质以上档次,气势不凡地占据了上海文学界的显要位置”(见《 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下册4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家文学刊物的发刊词就写到:“我们这杂志的内容确实是‘杂’的”(同上)当年的《太白》半月刊所设栏目就包括了“风俗志”、“ 杂志”、“时事随笔”、“科学小品”等,上至天文,下及地理,动物世界,植物王国,人类自身,宇宙之大,跳蚤之微,都有所涉。从横向上说,目前国外刊物的内容模式也不是那 种很单一的纯文学,如美国的《纽约客》周刊、《大西洋》月刊,每期中小说占的比重很有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和国外现在正在实行的办刊模式构成了改版中中国大陆文学期刊的 蓝本。
第二,文学期刊与文学史、与作家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在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期刊的办刊人从单纯地为政治服务的樊篱中走出之后,一直在为想象中的文学史办刊,在为作家办刊,也就是在为小圈子办刊。这是在一种误区中的行进。办刊人以为文学史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作家的写作也是可以不考虑公众反响的纯粹工作,界内人士的看法通过一定的媒体刊载而成为办刊的潜在标准。如今办刊人终于醒悟过来,文学史是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学史,它不是与社会生活相隔绝的存在,它是自然形成的文化历史。作家的写作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创造性劳动,文学作品构成一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内容。文学期刊要面向大的历史、面向作家和读者两个方面,将专业性文学的判断与读者的接受判断统一起来。换句话说,文学期刊不能仅仅是作家的实验场,不能仅以刊登不成熟的作品为标榜。
第三,文学期刊怎样由旧机制向新机制转换?
机制问题制约着文学期刊的发展,文学期刊由现在的不良状态向良性循环行进,其机制问题必然解决。旧的机制对应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但新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许多文学期刊的编辑部在内部机制这一方面还是大锅饭时的老样子,杂志社的机制刚刚有点刍形。旧的编辑部机制中人浮于事,没有真正量化工作指标、按劳按质取酬,人事制度是只进不出。在编辑工作中多是找米下锅、等米下锅,几乎不需要精心策划。新的杂志社机制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机制,它包括文学期刊的定位随机研究、组稿选题策划、编校制作系统、发行营销系统 、广告经营系统这几大部分。
三、新的世纪中国大陆文学期刊前瞻
经过调整后的中国大陆文学期刊将会在新的世纪中显示活力,一方面办得对路、对位的文学期刊会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由此又可以得到广告收益;另一方面文学期刊在与诸 种 现代媒体共存的格局中扮演一个母媒体角色。所谓母媒体角色,就是说由文学期刊可以衍生出其它文化产品,如改编电影、电视剧、出版图书、提供网上文化资源等等。
中国大陆的文化市场蕴藏着的潜力不可低估,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文学期刊的未来提供了光明前景。今天文学期刊面临的困境恰是迎接挑战的前兆,恰是面对新的机遇的黎明前夜,中国大陆的文学期刊只要有两万册以上的发行量就可以解决生存问题,而这两万册的发行量只需三十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平均销售六百多册就够了。况且中国的中等城市、县级市还在逐渐扩大规模,城市化是正在快速形成的区域模式。城市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文化消费比重的增大。
综合性时尚类、时事类刊物产业化道路的成功刺激着文学期刊也将进入产业化轨道。像《女友》、《时尚》、《新周刊》等一些综合性时尚类、时事类刊物已在中国大陆取得了产业化发展的成功,它们的经验文学期刊必然要有所借鉴。一旦这种借鉴与文学期刊自身的优势相结合,其效果或许会出人意料。
文学期刊主办人的年轻化趋势现在也已经形成,老一代编辑家随着年龄的增高已相继告别期刊,一批三四十岁的社长、主编目前正在一些主要的文学刊物中掌政。新老交替的顺利过渡,为文学期刊的现代办刊、经营方式的实行带来有利的条件。
未来的中国大陆文学期刊可能分化成三种状态:第一种是完全与市场接轨,在市场的竞争中生存发展。第二种是依靠政府拨款支持才能存在的,这类刊物可能主要是文学理论批评类的刊物。第三种是依靠企业或基金会方式支持的刊物,这种刊物可能具有民间化色彩。

1999年10月11日,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成立暨 “ 走向21世纪的中文媒体研讨会年会”主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