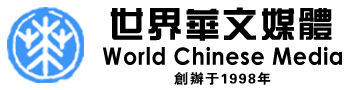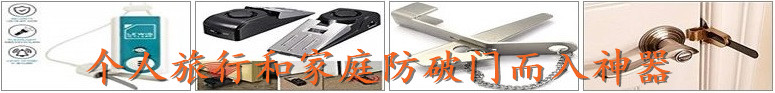杨益言叔叔的口哨声
杨亚平

《红岩》作者杨益言
许多人,包括国内大多数作家都不知道著名的《红岩》作者杨益言,是浑身充滿音乐细胞的人,他从中学生时代,就酷爱拉小提琴,技巧虽不如小提琴家那般炫技飞扬,但他的琴声是特别的柔美,特别的悠扬和抒情;在不能拉琴的“文革”十年恐怖岁月中,他就吹口哨,他吹的口哨声,是我听到的无伴奏口哨声中最有乐感、最优美、最深情的。
在上世纪的那个10年浩劫 ,著名作家杨益言身心受到了他人生中最惨重、最漫长的残酷摧残,但他在这10年艰难、痛苦的日子里,我常看到的是:
他每天在重庆市渝中区重庆村30号–重庆市作协门旁,那条陡坡道上打防空洞时,挥汗如雨地挥舞铁锤的身影。
我时常听到的,就是他重体力劳作后休息时,从口中吹出的那美妙动听的口哨……
《红岩》另一位作者罗广斌被“自杀”后,杨益言也被打成叛徒,并押送到边远又穷山恶水的”九锅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劳动改造三年后,杨益言带着极大的心灵创伤和身体的严重内伤回来了。
那是在1971年的夏天,杨益言叔叔刚缓慢地走进重庆村30号重庆市作协大门,当他艰难地登上门口那段很短的梯坎后,市作协最著名的造反派、也是当时文联重点培养的年轻作家杨世元就恶凶凶冲到杨益言面前,咬牙切齿地用手指着狂吼:”你回来干啥子?” ,杨益言轻声而坚定地说:”我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 ,突然,只听见“啪啪啪啪”几声,杨世元几个异常重的耳光就抽在杨益言的左右脸上,接着他又朝杨益言的大小腿和下身凶狠地踢蹬了几脚……并且嘴里还恶狠狠地骂道: “你个狗日的叛徒!还搞文化大命!!” 此时,我正在大门口玩,被这暴力场景惊呆了。
现在回想那场景,我只有从电影《辛德勒名单》中纳粹党卫军迫害犹太人时,才能看到这般残暴的场景。
杨益言叔叔是位性格内向还有点腼腆的人,他说话的语气和声音都是细言细语、斯斯文文的,他是如何经得起这般残暴的羞辱和暴打?
杨世元暴打杨益言之后,扬长而去,杨益言叔叔却蹲在地上一声不响地咬紧牙根,眼睛放射出愤怒……
我立马上去扶起悲痛万分的杨益言叔叔。
要知道这杨叔叔,他俩兄弟可是家父情义深厚的老友,他哥哥叫杨本泉,和家父是发小同学,在读初中时,他俩就共同创办了诗刊,解放后他俩合作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工厂短歌》;杨益言参加学生反蒋反美活动后被抓进渣滓洞,杨本泉多次找家父商量,他俩四处借钱,最后又一道去找警察局长后,才把杨益言保了出来。
解放后,杨益言和家父在市作协共事,杨益言叔叔两兄弟也是家父的常客。
我回家给父亲一讲,父亲大惊失色地说:” 这杨世元怎么打起人来了!太恶劣了!”
他最后叮嘱我:”你杨叔叔现在这情况,我不好出面,你有能帮的地方就尽量帮你杨叔叔……”
于是,我和杨叔叔之间的友情在他最艰难挣扎时建立了。
当杨叔叔从”九锅菁″劳改农场回来时,身体特虚弱,由于长期重体力地抬”连耳石″,他腰脊椎间盘受伤,解大便时都蹲不下去,基本上是半蹲半站,两支手还用力抓着两侧门框……
这是我经常在文联厕所看到他痛苦挣扎的情景;
他若在厕所看见我,就会喊:”亚平,扶我一下” 。我清楚记得,我问他腰杆怎么了,他说:在农场抬“连耳石”遭的,那石头太重了!
那几个月,市文联革委会给他安排的工作是打扫清洁,作协大院里的作家和诗人们都是他的老相识、老朋友,但沒有一人敢和他这“叛徒″说话,他也更不敢到任何一家串门,大家怕受牵连,他也更怕牵连大家。
杨叔叔时常在大院坝内石凳上用药酒揉背,只要看见我,他就会喊我帮忙给他揉。
杨叔叔的家住在团市委大院,距离文联约二里路,可他从劳改农场回来后,从未回过家,他给我讲,他身体来回走吃不消,还有就是他怕家人每天看到他这惨不忍睹的形象而伤心。
文联伙食团旁的一间脏黑的小房间就成了他的栖息之地。那房间我经常去,里面除了一张木板搭的床,什么都没有了,杨叔叔的脸盆和茶盅是放在窗台上的,洗脸的毛巾是挂在墙上铁钉上的……
半年后,杨叔叔身体基本恢复了,这时文联革委会给他安排了个重体力活一一 “打防空洞”。
一天,在作协院坝,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郭青(原文联伙食团的炊事员)把杨叔叔叫到面前严肃训斥: “革委会决定要深挖洞……从今天开始,你就打防空洞。″ 说完后就带着杨叔叔走到作协大门口路旁50米左侧石坡旁,用粉笔在石上画了个宽二米,高三米的白线……然后对杨叔叔说:”这就是你劳动改造的地方,文联这防空洞是革命任务,你必须坚决完成!”
我跟在他俩身后,只听见杨叔叔轻轻说了一句:”好吧”。
于是,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高温酷暑,每天,都能看见杨叔叔挥舞铁锤而挥汗如雨的身影,都能听见杨叔叔的铁锤叮当声……
最难忘的是,到了山城最酷暑的24个”秋老虎”时,杨叔叔干脆把湿透的背心也脱了,赤裸着上身,甩开着膀子挥锤。
看见著名作家这般下苦力的场景,看见杨叔叔那般坚忍不屈的顽强毅力,这给当时仍是少年的我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难忘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父亲也无数次难过地看见老友在像苦力般“打防空洞”。
一天,父亲拿了个老沱茶和一些水果糖,对我说:”你悄悄拿给杨叔叔,干万不要让人看见。”
那时杨叔叔吃饭喝水都是一个大铁茶盅,当时吃饭是在文联大门旁的两路口房管所搭伙。
那时,伙食团油水少,杨叔叔常叫我给他买卤核桃肉、或卤猪头肉或卤肥肠,一般是买二两,他只有这点生活费呀。杨叔叔反复叮嘱我,不要让别人看见,所以每次在洞门口给他时,特别小心谨慎,我买好后都是用牛皮纸包好的……
每当他劳累后,就会坐在洞内的石头上,赤裸着上身吹起口哨,那场景看着好舒心。
我现在回想起杨叔叔吹口哨时的特写镜头,真像著名油画家罗中立画中的大巴山朴实农民小憩的画面。
杨叔叔那口哨真是吹得好,我在此以前从未听到过吹得这般动听的口哨,无论是音色、音准、音质、乐感绝对一流。
听着他的口哨声,我就似乎看见了杨叔叔顽强坚毅的性格和战胜苦难的信心。
杨叔叔最喜欢吹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这口哨声,是杨叔叔在“文革”10年非人道摧残后唯一尚存的快乐,唯一黑暗中烛光般的慰藉。
我回家给父亲讲,杨叔叔的口哨吹得如何好,父亲也笑了,但我发现是他开心的苦笑。
那年代,我好难看见父亲笑一下。
大约三年后,那防空洞在杨叔叔的铁锤声和口哨声中慢慢形成了,它深有五米,宽约二米,高约三米。
我的天哪,那是蜚声全球的《红岩》作家杨益言用仅存的体力和战胜苦难的顽强信念,一手一锤用血汗和痛苦打出的啊!
杨叔叔打成的防空洞,一天都没有派上用场过。直到10年后,居委会把它租给了一位下岗工人在洞中卖小面,而我经常在洞中吃小面。有一次,杨叔叔来看父亲,我给他讲,你打的防空洞现在派上用场了,下岗工人在里面卖小面。杨叔叔笑了,父亲也笑了,他俩的笑声是开心的。
我在洞中问过杨叔叔,当年你被国民党抓进渣滓洞受过刑没有? 他说:”坐过老虎凳,我那时只是一个进步青年,我是参加了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遭学校开除后被抓的。”
我在洞中问过杨叔叔,你好久喜爱上音乐的,他说他在兼善中学上初中时就拉小提琴了,后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时就更喜欢拉了;他还记忆犹新地说,他在渣滓洞监狱里和难友们过春节联欢时,没有小提琴,他就拉二胡。
杨叔叔比家父小一岁,今年92高龄了,如今他衰老多病的身体,不仅走不出家门,还说不出话了……
六年前家父去世时,他已完全行走不便了,他派他最小的女儿代表他,向他的老友“山兄”做最后的告别……

《红岩》作者杨益言和其女儿
我曾把杨叔叔打防空洞和吹口哨的故事给杨叔叔最喜欢的小女儿讲过,她听出泪花来了…… 她惊讶地说:“父亲从没给我和我母亲讲过。” 我说,我一定会把这故事写出来的。
杨叔叔写的《红岩》早已蜚声全球,他塑造的江姐早已扎根于国人和世界华人的心底,由《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主旋律“红梅赞”,广泛流传并已成为中国歌曲中的经典。
杨叔叔在过去恐怖的10年岁月中,打房空洞小憩时,用仅存的一丝希望吹出的口哨声,今天仍然悠扬地缠绕在我的生活中,并早已铭刻在我的生命里。
作者简介:
杨亚平, 资深新闻编辑、记者,重庆市作协、四川省作协会员。
在《散文家》、《星星》、《四川文学》、《红岩》、《山花》、《中国诗人》、《绿风》、《诗潮》、《雪莲》、《中国青年报》、《香港文汇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成都晚報》、《西安晚报》、《昆明晚报》、《贵阳晚报》,《世界华文媒体》、《国际艺术新闻网》、《加拿大和世界报道》、《多伦多新闻网》、《法国和世界新闻网》、《纽约都市新闻网》、《美国西部新闻》《中国华人传媒网》等国內外公开发行报刊等媒体发表诗歌、诗评、散文、人物特写、报告文学近200万字。出版有诗集《浪花上的情结》、报告文学集《敬礼,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