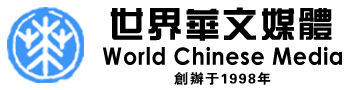关键词正名与历史感——文明更替的活的灵魂与现实可能
关键词正名与历史感
——文明更替的活的灵魂与现实可能
钱 宏
(Institute for GlobalSymbiosismPresident,Visiting scholar of Fudan University)
有朋友读了《生態要统筹,共生是灵魂——读十九大报告,兼论中文“共生”概念的英文对译》,提醒我“你将其视为灵魂(共生为魂),人将其视为点缀(和谐共生)”。他举例说,“对比一下两个提法差别: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一,“要加快生態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態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態环境监管体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后面没有出现‘共生’。”第二,“结合你关注的外文翻译(十九大首次专门找了十三个国际翻译),却没有‘共生’对译。必须看到,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共生价值观真正走进全球领导人的思想深处,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你作为思想倡导者,要有心理准备。”
然后,这位朋友又发给我一个新闻:国内首家飞地孵化器集群“大农空间——(长沙)大农孵化器总部基地”(以下简称“大农空间”)项目盛大启动;同时,“千名博士计划”(金桥)湖南创新中心举行揭牌仪式。为帮助边远县市克服区位优势不够、高端人才紧缺、新兴产业基础薄弱、发展现代农业先天不足的短板,“大农空间”帮助各县在长沙建立“农业科技孵化器”,打造“注册在县城,办公于省会”的新型飞地孵化发展模式,有助于入驻的各县城共享省会城市长沙的人才、产业、资金、信息、教育、医疗等各大要素优势,遵循未来先进的共享农业发展观,城乡在人才、资金 、技术、信息、配套等资源将会得到高效流动和配置,通过凸显和发挥现代农业集群效应,不断孵化边远县市产生一大批科技型农业企业和农业品牌企业,研发一大批有价值的农业技术转化成果,全力拉动当地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从而推进各县城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大农空间”是由大汉集团、大农股份以及一群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的博士、教授投资运营,首期建设50000平米,将聚集50个县城孵化器+50所高校及科研院所(农业方向)科研成果转化空间。“大农空间”三年行动计划(6个100计划):县域孵化器–100个贫困县孵化器;2、高等院校科研孵化–100所高等院校 科研成果孵化空间;3、农电商孵化–100个城市电商特色馆;4、城市服务店孵化–100个城市服务中心(农特产品店);5、农产品品牌孵化–100个农业品牌;6、标杆企业孵化–100家农业标杆企业。
我对这位朋友说:了解你善意的提醒,谢谢!
这个“大农空间(6个100计划)”,本质上还是工程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必然会遭遇“制度-文化-人性”非良性循环条件下的权力的傲慢和愚蠢,如果真实施,结果将再次证明是个“广种薄收”的大忽悠。
在不余遗力使人受益的意义上,我秉持“直钩钓鱼”的態度和“随遇而安”的快乐原则(因为我从没有把我的思想与我个人生活改善挂钩,所以思想对我来说,就像我青少年时代给人治好了病不收钱一样,十分快乐)。所以,我的思路一以贯之,不受任何个人(包括自身)和组织(包括中共)变化的影响。
人们(包括当局、新闻媒体、翻译、城乡官民)的共生觉醒,只是个时间问题,好东西有时需要危机倒逼。眼下的情况,无论人们真心诚意还是言不由衷抑或醉翁之意用什么样的修辞手法装疯卖傻,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明摆在那里,明白人也有的是,最后都要走到以下认知上,才能真正参与和开创新时代。
顺着19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基本方略”第九条“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马克思“物质变换”过程的双重意义——一是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二是人类社会内部的物质变换,马克思用它分析资本的循环过程和商品的交换过程。“物质变换”既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也包含了特定的生態意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中国在北有“雄安新区”,南有“鄱阳湖生態文明实验区”——两大功能迥异本质一致的实验基地,需要理一下思路,获得一点历史感!
中国作为工商文明的后发国家,采用“边区”“特区”“园区”集中资源(力量)的实验模式,是可计量成本最低而见效最快最便捷的方式。从战时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实验的“陕甘宁边区”,到奠定中国工业基础的“苏联援建的156项目”分三大片区落户;从单纯招商引资的“深圳、厦门特区”,到土地财政和中央商务区(CBD)城市化样板的“浦东新区”;从乡镇企业一枝花的“闽南、苏南模式”,到走出去引进来的“浙江模式”;从分蛋糕的“重庆模式”,到做大蛋糕的“广东模式”;从全国省市区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冠以“国家战略”的经济型特区、试验区、综合治理试验区、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创意园区,到以开放促改革的“上海自贸区”,以及所谓“特色小镇”的一窝风;从圈钱动机的“沪深股市”,到渐见些微生態意味的“绿色金融”……中国各级官员、专家、企业家们,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思维路径依赖与利益格局羁绊,连“生態文明建设”,也多半理解为“生態经济建设”(2008年2月我给江西省委省政府建议设立“环鄱阳湖生態文明实验区”的建设,就被改为“生態经济实验区”上报和批准)。
鉴于此,进入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治理,中共乃至中国精英人士,必须在思维方式上有所改变。
改变思维方式的首要工作,就是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正本清源,亦即“正名”工作优先——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且,这项关乎中国能否顺利迈进习近平新时代的基础工作,可以借助某个新闻事件,顺势将其拓展到全新闻领域的语言净化上来,掀起一场不动声色的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当代正名运动”,可以无风险地做出“蝴蝶效应”来(参看钱宏:《一切从语言的正名与改变开始》,2007)。
我们来读一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中的第九条。习近平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態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態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態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贡献。”
习近平在讲“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时,首先强调的是“建设生態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接着以“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贡献”结束。
这就从基本概念上澄清了“生態文明”的本义,不只是“保护生態环境”,即不只是“conservation culture”,而是“ecological civilization”即生態文明“不仅包括保护自然资源的内容,而且包括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容。”
早中共17大提出“建设生態文明”之初,刘仁博士2008年2月就在博客中著文列举三条理由,说明将中文“生態文明”翻译成“ecological civilization”也许更专业一些。他的四条理由是:第一,近20年来,国内外专业研究领域对“生態文明”即等同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均持一致意见;第二,“生態文明”中的“生態”或“生態学”(Ecology)一词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自然科学特点;第三,“生態文明”在国内两种学术排列中都应该译成“ecological civilization”。刘博士的结论是,“生態文明”翻译成“conservation culture”不妥(参看新浪网刘仁博士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96e7101008556.html)。
当时,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一片欢呼声中,还有刘仁博士这样认真的人,对“生態文明”的概念作正名的工作!中共十八大已经将“生態文明建设”提到“贯通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高度,当然是ecological civilization之意才能承载得起。
但是,看到十九大新闻中心发给各国媒体和记者的《十九大报告》在与“生態文明”密不可分的,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基本方略的“(九)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英文版翻译稿上只有这样的意思“9.Ensur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明显漏掉了“共生”(Symbiosis或Symbiosism)这个关键词时,我不得不在10月18日当天写出《生態要统筹,共生是灵魂——读十九大报告,兼论中文“共生”概念的英文对译》一文。
因为这种“漏译”,不仅是翻译者头脑里有没有“共生”的概念,而且直接涉及对“生態文明”的理解和怎样“建设生態文明”?“把生態文明仅仅理解为生態环境、生態经济”将有什么现实问题?以及“生態文明建设的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怎样体现?等一系列实践问题。
我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生態文明建设”的关系,作如是解读,就教方家:
生態经济(Ecological Economy ECO)是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基础,生態政治(Ecological politics)是生態文明的上层建筑,生態文化(Ecological culture)是生態文明的支柱呈现,生態社会(Ecological Society)是生態文明的自然风范,生態组织(Ecological Organization)是生態文明的结构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马克思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伴随每一次文明生態更替,都有其应运而生的哲学。从人类文明更替的活的灵魂看,正如作为农耕文明(Farming & Reading civilization)的灵魂是“和谐”(Harmony);作为工商文明(Industrial & Commercial civilization)的灵魂是“权利”(Rights),都是哲学概念一样,作为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灵魂的“共生”(Symbiosis),必定也是一个哲学概念。
生態文明新时代的精神精华、活的灵魂,就是追寻动力学智慧与恊同学智慧实时均衡制衡平衡的可能之共生哲学(Symbiosis Philosophy),将是当代中国人向世界贡献“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的开始。
我们不妨用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中文“共生”或“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所以,共生哲学,讲的是从而由此发现和展开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有无相生”、“天人和合”与“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的永恒创生的故事。
共生哲学,是与中国生態文明建设应运而生,作为生態文明的灵魂,既是一整套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一种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一种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態,也是一种可践行的当代性生产生活生態方式——即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的生活方式。
所以,只有在共生或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意义上,才与习近平19大报告讲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建设生態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内容是吻合的。
因而,可以一以贯之地简捷地说,生態经济亦即共生经济(Symbionomy),生態政治亦即共生政治(Symbiopolitics),生態文化亦即共生文化(Symbioculture),生態社会亦即共生社会(Symbiosociety),生態组织亦即相对于共同体(Community)的共生体(Symbiosome)组织。
这样,我们来分别看看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方式”的变化,以考量一下我们的历史感!
农耕文明(Farming & Reading Civilization)的灵魂是“和谐”(Harmony),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方式比较简单,虽有天灾人祸及生产力低下的稀缺性,总体上依赖于生態系统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联系的良性循环(人的衣食来自大自然,而人的排泄物又以肥料的形式回归土壤)。
工商文明(Industrial & Commercial Civilization)的灵魂是“权利”(Rights),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方式复杂而集中,以人为本自由理性催化生产力发展大规模掘取自然资源,从集中生产交换并任意排放污染物的生产方式,到集中消费并丢弃垃圾的生活方式,都是单向线性的从而形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循环断裂、以及人类社会经济循环断裂和城乡失衡的“世界性经济障碍”,必然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并招致自然报复。正如安联(Allianz)首席经济顾问、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埃尔上个月著文所言:“全球经济正在瓦解,最糟糕结局或将出现”。而从地球生灵共生的视角看,经济危机乃至于经济“瓦解”的本质,就是生態危机!
不妨对照一下前面提到的“大农空间(6个100计划)”,不难发现设计者头脑中,很难说有“生態文明建设”这根弦,果如此,这些主(肇)事者们又何谈紧跟习近平新时代“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灵魂是“共生”(Symbiosism)。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方式,必然是在生態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原理及其系统工程与恊同发展方法,通过参与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开放过程,改变生产-交换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高效挖掘和适度利用既有资源潜力(在一定时空条件下, 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化石能源,及有限性、可再生资源,也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管理制度等所有为实现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开放而投入的要素),提高“资源生产率”【生態效率、资源效率、资源强度和每单位服务的物质投入 ( material input per service unit,简称MIPS)】及“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发展高能效、低能耗的循环经济业態,让“社区、市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建设符合自然承载力与人类身心灵健康的美丽生活,实现自然生態与人类生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共生”。
今天上午看了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新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有一种感觉,不妨说说,这就是:中国高层从14大清一色的工程学(计量、逻辑、建模)的经济学治国,经过15、16、17、18大错落,开始过度到19大清一色的伦理学(道德、法律、心理)的经济学治国,将成为中国经济学基本理论创新的一个现实大拐点。
这一转变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民本位经济学”导向和经济学对象从计量的逻辑的建模的“理性人”(利润最大化指数)权重,到生气、活力、血气甚至“无知近乎勇”的“动物精神”(信心指数)权重,很吻合。这也是我2017年5月9日,我应邀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作《“社会论”的共生经济学如何接着新老“资本论”说?》预言“社会学将取代传统经济学显学地位”的又一个验证。
日前,看了各地代表谈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我写了《毛邓习三个时代的基础、问题与前景——从魏杰<大会之后,中国将大规模调整经济布局(深度长文)>说起》。我想,囿闭于“宏经”与“微经”中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将再次看不懂中国经济!
2017年10月25日于上海
附录:
一切从语言的正名与改进开始
题记:此文写作时,一段内容是对央视几位名嘴的批评,现予删除,呵呵!昨天在一读书会上与央视新闻[1+1]主编刘明君先生结缘,正好把前几天看张泉灵主持的节目时产生的一个设想与他交流:我感觉央视有一件事,可以无风险地做出“蝴蝶效应”来,这就是把近期已经开始做,并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的为“老年痴呆症”正名的工作,顺势将其拓展到全新闻领域的语言净化上来,掀起一场不动声色的为重建社会服务的“当代正名运动”……只要开始干,我相信有央视各频道和栏目主创者的智慧和技巧,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到最棒,做出远远超过1978年光明日报那篇评论员文章的社会效应来!
钱宏2012年10月29日十八大前夕
我们注定要经历并参与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全新转折点,变化、改变需要智慧引领,中国和世界都需要新的智慧引领向前,而这一切都是从语言的改变开始。所以,关注语言生活的变化状况,无疑有助于“语言的改变”,但我们的着力点显然不会止于此,否则,伟大的“路德改革”就将被目光短浅的人们批评为“冒失”。
然而,历史却公正地评价了马丁•路德的伟大功勋——他对德语的纯化、规范、通俗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德意志民族,将其承载、复兴、创造的思想理论和哲学传遍了欧洲……所以,我坚定地相信,从人类新的生产、生活、生態转变中锤炼出来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亟需新的语言来承载。因此,我们在关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同时,积极、主动、自觉地对我们百年以来官方语言、用语进行一番全面梳理、规范和纯化,实属一件必要而必然的事情。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创造,是由人类之间最初无意识的声音交流演变而来的一种特定的表达方式。虽然动物之间也有声音的交流,但只有人类才会把无意义的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来表达某些具体意义,通过特定的组织方式来表达和记录人类特有的思维活动。随着人类千万年的发展,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交流工具,从最初的简单交流逐渐演变为一种复杂的系统。按照背景主义的观点,对语言可以按照三种不同的形態进行分类:一是按其物质文明形態分为:文字、语汇、声音、符号(图腾、徽章、Logo)等;二是按精神理念形態分为语义、象征、指令等;三是按其工艺组织形態分为语法、规则、约定俗成、语境等。另外,语言演变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其种类和数量的变化上。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3000~4000种语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100万的语言有100种左右,超过5000万人的有20种左右。
语言本来是人类自身的发明和创造,是人类交流的主要方式,也是人类传递经验的主要方式,是与社会文化密切相连的,因而被创造者——语言,逐渐开始发挥它对创造者的反作用。人类的一些文化传统,通过语言的进一步加工,部分很好地传承了本来的意思,但有一部分由于特定的原因,可能跟具体的社会情况相结合,产生变异,而这种变异有时会被吸收到产生这些变异的文化传统中去,并再一次的被后世所承继,一代又一代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因而虽然语言是人类自己的创造,但这个被创造者并不是无生命的东西,它自己也在不断发展并影响创造者,要真正探究和表达人类自身独立的观念,就必须对表达观念的有生命的语言进行刨根究底的研究,从而更加精确地表达人类要传达的“心声”。
中国在1911年之前两千多年间的宗法专制时代,庙堂之上传播的都是“以民为本”的君权理念,在君主与臣民“信息不对称”的年代里,也形成了一整套官方和官场的“高端”传播用语,在语言形式上,主流媒体使用的基本上是一般人民不容易明白的“之乎也者以焉哉”这些个所谓文言。
1912-1921年,孙中山派蒋介石到俄国考察之前,中国处于一个看似理念混乱而新的社会生机孕育时期,共和、公民、民权、民生、宪政、政党、民主、科学、自由、立法都开始被传播流行开来,只是还没有真正落实到有效的制度安排,主流媒体开始使用年轻人喜欢的充满活力极具批判性的白话,即复兴了过去不为称道的杂剧、小说家言。
1922-1937年,中国进入一个国家主流媒体的“党国”(party-state)理念与社会传媒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理念相互叫板的互动时期,尽管国内战争频仍,可语言上已经有了很大创新,并在中西文化的交融整合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日本的侵略,一切都被严酷地打断了。
1949-1978年,由于世界1945年后出现“两大阵营”的格局,而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社会传播语言单一化,导致词汇的贫乏和定格化,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当描述人的笑容时,总是用“灿烂”,在比喻祖国时,总是用“母亲”(党是“妈妈”),在中学的课堂作文上,不管你写作的是什么题材,结束前都要点题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我曾经把它叫做幼稚园“乖孩子语言”或“喉舌性语言”。
1978-2005年,中国进入主要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资本实践。1990年代开始,由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一反既往,“说新闻”和王朔小说的出现,以及后来网络语言、手机短信语言的滥觞,而进入一种解构性或享乐性的“消费性语言”或“娱乐性语言”充斥视听的时代。所谓“空洞的危言耸听和低级的煽情主义结合到了一起”,正是“消费性语言”或“娱乐性语言”的表现。说这是一种由中国社会的“先富阶层”、商家和传媒人(广告人)及“港台岛民”搅拌起来的奢侈而空洞的语言滥情现象,也并不过分。
无论“乖孩子语言”或“喉舌性语言”和“娱乐性语言”,在占据人们思维空间上取得怎样的辉煌胜利,但它们同样是匍匐在地上,而望不见新思想的天空。如果说“娱乐性语言”是卡夫卡说的将“情感的枯燥掩藏在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来逗你玩儿,那么,“喉舌性语言”,则是将“思想的贫困掩盖在煞有介事的气势之下”唬人。都只是充当了某种既定利益意志(动机)或设定程序的“传声筒”。可是,互联网和卫星电视时代的到来,延续了几千年的“凭借信息不对称”对受众进行愚弄的统治,将成为不可能,“统一口径”的传声筒式的传播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所谓“网络民主”传播时代。于是, “语言的变革”也就是势所必然。
语言是思想、理念的空气,思想理念的天空有赖于语言的支撑,普及和传播的效果和效率,首先在于传播者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旧有的思想理念,不足以催生和包容清新精准的语言,而旧有的语言,更不足以支撑和显现新的思想理念蓝天。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社会传媒人,记者、编辑、作家、主持人、名人笔下和嘴里,充斥着与“和解共生”、“多样共生”价值理念相悖用语的传播氛围中,能够真正做出与民主、科学、法治、人权精神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并在全社会得到实行。在这个意义上,说“理念比制度更重要”一点也不过分。那么,就让这一切从语言的正名和改进开始吧。
端庄、清晰、中立而精确的语言是必需的,这正是一种基于“建设性思维”的时代呼唤!
转变观念必定要改进我们官方文件、文本和新闻传媒中已经习惯了的语言、用词、用语(我在1995年作过一个统计,这些语言70%以上来自日本人对欧美语言的转译,带有浓重的日本文化色彩)。如用“执政”、“共和”,取代“专政”、“一元化”;用“领导人”、“国务活动家”、“政府首脑”,取代“领袖”、“掌舵人”;用“行政长官”,取代“领导”;用“官员”、“公务员”,取代“干部”、“父母官”;用“人民”、“民众”,取代“老百姓”(歧视性特别明显却用滥不觉)、“群众”;用“规范”、“服务”,取代“领导”、“带领”;用“公民”、“纳税人”,取代“子民”、“老板”;用“人本”、“兼爱”或“仨爱”、“民主”,取代“民本”、“仁爱”;用“良智”、“公意”取代“党心”、“民心”;用“文明”、“和解”取代“野蛮”、“斗争”;用“共生”取代“公有”“私有”……总之,与现代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不相适应的,需要改进的语言和用词很多,需要进行全面梳理。正名工作,可以精选顺序一个一个地进行,这里只是顺手拈起,抛砖引玉。
的确,2006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超越过去所有时代,进入一个“以自主创新为出发点”的社会建设和生態文明时期。在经济方面,中国将超越过去20多年以“效率为主导的改革”,而进入“以公平为主导的改革”,并继续效率改革与国际接轨;在政治方面,中国将开始实现“宪政文明”;在社会方面,中国将全面开展“公民社会”的建设,从后工业社会,进入前生態社会;在文化方面,中国将接纳融合人类世代为之奋斗的“普世价值”,从现代主义进入当代主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以“自主创新”的建设性思维方式为出发点。而“语言的改进”就是这一出发点的先导。
在我们的主流文化主流传媒的词典里,甚至在最新版的《辞海》里,还找不到“公共空间”,甚至“公众”这些个词语。但是,且不说中国早已是“共和国”,就说现在,在中国已然“入世”5年、经济全球化、传媒跨国化,从而建立世界性“公共空间”亦是势在必行的今天,我们中国公民还不需要享有自己国内的“公共空间”吗?我们的主流媒体和传媒人,还有理由排斥建立“公共空间”的思想平台和制度平台并习惯使用“公众”、“公民”、“公仆”、“公权”……这些现代语词吗?
哈贝马斯说,公共空间不仅使一系列特殊利益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制度化,而且还使一种对政治事务进行公开、理性和批判性讨论实践制度化,后来他在一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称这种讨论为“沟通行动”。在他看来,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模式的潜在功能。公共空间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它一部分是在日常对话中建构起来,“私”人们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公”众社会,之后,他们不再作为商人或专业人员从事他们的“私务”,也不像法律专业人员那样受制于国家官僚机器法律管理并且被迫服从。
这不正是我们当前“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吗?文化交融,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人类沟通行为总是要借助一定的平台作为媒介才能进行。
“公共空间”的建立,源于18世纪。从18世纪的英国咖啡馆、法国的沙龙、德国啤酒馆,到各种各样的国际性论坛和娱乐节目,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到卫星传播,直到大型立体的跨国传媒的出现,人类通过这些沟通平台,逐渐从“私”人一步步走向“公”人,从“受众”变成“公众”,世界由小变大由大变小,文化从一元走向多元融合。这个跨国性的公共空间,远远大于哈贝马斯式的公共空间——即国家和社会的调解空间,这是一个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的调解空间、和解空间及融合空间,人类将由此走向“世界大和”,走向共生。
我们今天终于说出了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可实际上我们只是基于对痛苦历史有反思,从反向思维上比较笼统地明白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专制不是社会主义”、“野蛮不是社会主义”、“恶耗不是社会主义”。那么,真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要做,还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公共思想平台和公正的制度平台上,这就是作为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基础之“宪政”理念的普及和“宪政”制度的落实。而这一切改变,还需要“从语言的正名和改进”开始。语言的变革,非易事,一旦有了实际的社会性改进和改观,将功莫大焉。
2007年11月3日
文章来源:全球共生研究院 2017.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