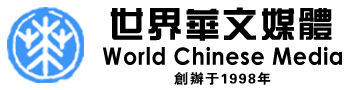东南亚华商与经济民族主义

作者:梁英明
21世纪将是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这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经济水平差异的国家或民族之间,以及经济利益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必然存在各种矛盾和冲突。因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的必然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处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东南亚华商,在国际上同样必须应对全球化与民族主义这两种力量的激烈碰撞。与此同时,他们在各自国家内部还要受到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原住民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压力。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东南亚华商曾经走过怎样的艰难曲折道路,他们又将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国内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复杂环境,谋求自身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原住民优先”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其后,除了印度支那国家和缅甸由于战争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以致制约其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外,在东南亚各国经济迅速成长的过程中,都使当地华商获得了发展的有利时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东南亚各国一批华人大企业集团的相继涌现,就是华商经济实力增强的一种象征,东南亚华商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就,无疑主要得益于战后这个独特的历史机遇。
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迅速成为东亚地区的一个庞大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是历史给予东南亚国家及华商企业的又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东南亚各国企业(包括华商企业)必须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及时搭上“中国快车”。
东南亚华商企业在这两个阶段获得的迅速发展,除在华人占人口大多数的新加坡以外,都在相关国家的原住民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战后东南亚华商的第一个发展阶段(4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各国政府曾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制度、法律、条例和政策,以国家的名义建立起一批政府拥有的大型企业,同时宣布扶植和保护原住民的私人企业,限制外侨企业的发展。例如,1959年菲律宾总统提出“菲律宾人第一”政策,并据此制定了“米黍业菲化法案”和“零售商业菲化法案”; 1960年老挝政府实施“禁止外侨经营12种行业法令”; 1971年马来西亚开始实施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积极扶持马来人向工商业领域发展,给马来人提供“保留地”以及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内的多种特权; 1948-1960年间,缅甸推行“企业国有化运动”; 1949年,泰国开始实施“保留职业条例”,保留给泰人的职业逐渐增多,到1960年时达到17种; 1950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实施照顾原住民进口商的“堡垒计划”,1957年实施“15种工业印度尼西亚化法令”,1958年实施“雇佣外侨法令”,直到1959年实施限制外侨经营零售商业的第10号总统法令; 南越政府从1948年至1956年间陆续实施多种限制外侨经营大米、布匹等商品的法令, 等等。
上述各国的法令、条例,虽然针对各自不同的情况而制订,但显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方面,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前的东南亚各国华侨仍具有双重国籍身份,他们仍被视为中国公民,这些法令条例均以保护东南亚本国公民利益的名义颁布和实施,因此显然是以限制华侨拥有企业的发展为其主要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度支那国家中,华侨与当地原住民之间通婚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经营工商企业的华侨,往往可以用他们的原住民配偶作为企业所有人,从而可以避免受到这些法令、条例的限制而继续经营。结果,除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缅甸以外,这些法令、条例在东南亚多数国家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在印度尼西亚,1959年的总统法令导致几十万名在乡镇地区的华侨小商人离开他们的居住地而回到祖国。在马来西亚,马来族对自己在经济上所处弱势地位的不满情绪,终于酿成1969年的“五·一九种族冲突事件”,并促使马来西亚政府实施进一步保护马来族特权的“新经济政策”。即使在这两个国家内,限制华人企业发展的做法也没有完全达到政府预期的目的。至于缅甸的国有化政策,其作用并不限于华商企业,而直接影响到缅甸国民经济的发展,华商自然也不能幸免。
在战后东南亚华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形势和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战后30 多年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华侨已经陆续加入居住国的国籍,成为各国的华裔公民。华侨政治身份的转变使各国原有限制外国人经营某些企业的规定已丧失了对他们的法律效力,这对华商自然是一个有利因素。然而,法律并没有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东南亚国家的原住民统治集团中,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种族主义仍然是他们确保政权获得原住民拥护的重要政治基础。因此,这些原住民统治者往往夸大和强调华裔公民在本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的强势地位,而以维护原住民的经济权益作为他们的政治口号和施政目标。
其次,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后,中国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给东南亚华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这也使东南亚一部分华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彰显自己的民族自豪感甚至优越感。这些因素增加了原住民政府对华商与中国扩展贸易、投资关系的疑虑。正是在这一新形势下,有些人开始宣扬所谓东南亚华人将“重新中国化”等说法,从而在某种意义上为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从法律上来说,原有的华侨既然已成为居住国的公民,他们自然应该具有与其他族群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而在东南亚各国同中国已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投资活动也在逐步扩大的情况下,东南亚各国华商与中国企业间的交往合作应该是完全正常的商业行为。因此,上述对东南亚华商的种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东南亚国家的华商早已长期定居当地,许多华商家族甚至已经世代生活在那里。他们的前途和利益已经同居住国息息相关,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后代必然将更加深深地植根于他们居住的国家。因此,东南亚华商是不可能“重新中国化”的。尽管作为华裔,他们与祖籍国之间必然还会有文化上的联系,但是不应将文化认同看作一种“政治效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出国经商,他们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与居住国人民发生商业纠葛或利益矛盾,有的地方甚至酿成流血冲突,一些华商被迫离开这些国家而回国。我们可以从各种新闻媒体中看到这类报道。然而,东南亚各国华商与上述所谓新华商的情况不同,他们并没有以推销中国的廉价商品来占领当地商人的传统市场,更不是依靠假冒名牌或盗版侵权来攫取暴利。他们绝大多数是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而赢得顾客认可的。然而,由于经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东南亚华商在企业经营等方面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华商在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活动也往往被官方舆论抨击为国内资本的“外逃”,或甚至被指责为缺乏对国家的“效忠”观念。这说明,尽管东南亚华商在法律上已拥有公民的身份,却仍然被当作与所谓原住民不同的“外来者”。因此,在一些国家的任何一次国内经济危机或政治动乱中,华商都可能成为替罪的羔羊。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首都爆发的大规模抢劫和焚烧华人商店的骚乱事件,就是一个显著的证明。
世界各国关于民族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在东南亚地区,有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虽自称只有一个民族,但实际上同时存在着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这是无可讳言的现实。东南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并建立统一国家的时间还比较短暂,它们建设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有些原住民政权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号召,而以经济种族主义为实际内容的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在这一情况下,某些华商大企业采取与原住民企业家或官员“合作经营”,或以其他形式直接向某些官员行贿而获得某些商业利益,是他们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可以说,在公民中区分所谓原住民与非原住民,而又给予原住民商业优惠越多的国家,在官员权力越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官商勾结”现象可能越带有普遍性。在这些国家里,华商也往往被抨击为造成政府腐败的主要责任者。实际上,经常向官员行贿的华商实际上只是极少数大企业,而一般中小企业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任何国家的“官商勾结”现象中,“官员”总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商人”则只能是从属的一方。因为“官员”拥有的无限权力才是“官商勾结”现象存在的决定性的因素。在菲律宾等国,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甚至公开要求某些华商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苏哈托在统治印度尼西亚32年中,确实与某些华商大企业集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这些大企业中拥有一定股份。这使他的家族和部属得以聚敛大量财富。在他下台9年后,清查和追缴苏哈托家族贪污所得的呼声仍不绝于耳,但是法律诉讼仍毫无进展。有些人认为苏哈托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建设有“重要贡献”,因而“功大于过”,并以此为他的贪污腐败罪行辩护,也有人以苏哈托家族的贪污罪行“证据不足”为由而为他开脱罪责,更有人认为苏哈托过于信任某些华商大企业家,而被他们所利用,又由于这些华商大企业家的“背叛”,才迫使苏哈托下台。 这些言论将苏哈托统治时期的贪污腐败完全归咎于华商,同时又将华商描绘为一群背信弃义的奸诈之徒,显然是出于对华人的种族主义偏见,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制造误导社会的舆论。
民族主义的对立
经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另一个作用,是原住民统治集团企图将它作为对华人实施全面同化政策的一个工具或手段。但是,它显然并没有能够达到这一预期的效果。历史证明,民族融合只能通过各民族自愿的和平交往方式来实现,它必然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强制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只能激起被同化民族的抗拒,从而增强被压迫者的凝聚力和民族主义精神。对存在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国内不同族裔间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对立,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可能带来积极的效应。
即使处在苏哈托专制政权的压力下,禁止使用华文、华语,取缔所有的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不准华人庆祝本民族的传统节日,甚至强迫华人改用印尼人姓名,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可能消灭华人的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相反,东南亚一部分华商由于感到在国内受到某种歧视和压制,于是企图在国际上寻求更大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希望获得生活在异国的同胞们的合作与帮助。这样,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由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华人社团发起,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华人社团联谊活动,如1971年开始举办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1981年开始举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1989年开始举办的海南乡团联谊大会,1990年开始举办的世界福州十邑同乡大会,1993年开始举办的世界广东同乡恳亲大会,以及1994年开始举办的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等等。这些活动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以乡亲组织的名义举办的,一般每两年举行一次。此外,还有许多宗亲会举办的类似活动,难以尽述。其次,这些活动的实际内容是希望建立华商的国际联络网,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第三,这些活动大多数是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某些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泰国)等地举行的,它显示了中国政府及中国企业所起的主导作用。
然而,我们在看到这些频繁活动的同时,也不难发现它们对推进东南亚华商在国际上的合作与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仍然是很有限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国际华商网络并没有因此建立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起和推动下,出现了超越宗乡和宗亲关系的新型国际华商联谊活动形式,这就是世界华商大会。1991年8月,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约800名华商出席了盛会。其后,大会每两年分别在不同地点举行。2001年在中国南京市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吸引了3000多名华商参加。2007年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华商大会的参加人数甚至达到5000人。比起华人宗乡会馆或宗亲会馆举办的联谊活动,世界华商大会无疑具有更大的规模,更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是迄今为止,世界华商大会并没有获得与其组织规模及耗费的财力相对应的商业成果。与此同时,在东南亚国家的原住民政府及其企业界,对世界华商大会等活动却表示了保留和质疑的态度。他们认为,各国华商的这类活动带有某些种族色彩和排外性质,不利于各国华商与所在国家的其他族群企业界的合作,不利于东南亚国家的国内资本积累和扶植原住民工商企业发展的国家政策,也不利于这些国家的华裔公民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历史趋势。
然而,资本的国际流动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出现的结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陈嘉庚企业集团、胡文虎企业集团、印度尼西亚黄仲涵企业集团和泰国陈弼臣企业集团等等就已开始在香港、澳门等地开拓跨国经营。大约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东南亚国家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东南亚一些华商大企业集团又纷纷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建立跨国企业集团。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华商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已有58家,其中26家的主要股东为马来西亚华商,10家为新加坡华商,14家为印度尼西亚华商,7家为泰国华商,1家为菲律宾华商。他们在香港商界被戏称为“南洋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这58家企业的总市值约为315亿美元,占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5.6%。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华商在香港的企业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直到2001年才有所恢复。2005年,名列香港《亚洲周刊》公布的“国际华商500”的企业总市值比2004年增加21%,2006年扣除新上榜企业效应,当年500家国际华商企业的总市值仍较2005年增加12.6%。 但是,与同期在香港上市的华资企业总体情况相比,在香港的东南亚华商业绩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扩展。2005年,在“国际华商500”中,有144家东南亚华商企业榜上有名,到2006年,上榜的东南亚华商减少到101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这些东南亚华商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被评论为“仍缺乏国际视野”。
无论如何,东南亚华商通过香港进军世界的举措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它与局限于华商之间的联谊活动不同,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特点。首先,东南亚华商在香港建立新的企业主要着眼于企业的市场扩展和利润增长的需要,也就是遵循“在商言商”的原则。因此,对东南亚华商进军港、澳地区的动机赋予过多民族主义含义是不符合实际的,尽管文化、语言和习俗等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完全否认。从根本上来说,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给东南亚华商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相对自由宽松的商业环境和严格的法律制度也给东南亚华商的利益以更加确实的保障。而香港作为跨国企业进军中国大陆的桥头堡的作用,更是其他地区所无法取代的。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而不是新加坡或其他地方成为东南亚国家投资发展的首选之地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香港的东南亚华商往往采取与港、澳资本及其他外资合作的方式创建新的企业,再以这些合资企业的名义进入中国内地或返回东南亚国家投资。还应注意的是,在香港的一部分东南亚华商企业并非完全属于华商资本,而是包含有某些东南亚国家原住民的资本在内。例如,印度尼西亚华人企业家林绍良家族和林文镜家族在香港建立第一太平集团时,印尼原住民企业家苏德威卡特莫诺(Sudwikatmono)家族和伊卜拉欣·里斯贾德(Ibrahim Risjad)家族就一共拥有20%的股权。
第三,东南亚各国华商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大多由家族的第二、三代经营。他们当中包括印尼华商林绍良之子林逢生,李文正之子李棕,黄奕聪之子黄鸿年,马来西亚华商郭芳来之子郭令灿、郭鹤年之子郭孔丞,新加坡华商黄廷方之子黄志祥,泰国华商陈弼臣之子陈有庆,谢易初之子谢国民,等等。这些新一代华商曾受过高等教育,具有新的经营理念,熟悉国际商业环境,他们必将在其企业集团走向国际市场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融入社会,互利共赢
当今世界各国对民族主义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界定或理解,对民族主义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褒贬不一。这里不予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在东南亚各国,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是历史的遗产,是政治的现实。然而,某些国家的原住民领导人认为本国只存在一个民族,即所谓原住民族,而拒不承认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存在。有些国家则将本国公民分为不同的种族集团,分别实施不同的政策。因此,就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奉行的所谓民族主义实质上只是原住民的种族主义。只要这些观念没有改变,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种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华商也必然首先成为受害者。
现代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历史的合理选择。不同民族之间只能通过长期的交往而逐渐融合,而不是通过相互排斥而保持对立。在昔日的华侨已转变为各国的华裔公民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唯一出路是融入社会,落地生根。当然,这一发展进程不会是很顺畅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力日益增强的影响下,东南亚国家原住民和华裔族群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可能高涨,从而促使民族矛盾加剧。
在这一情况下,针对某些华商喜欢炫耀财富、与中国官方关系过于紧密等问题,仅仅呼吁华商应该“谨言慎行”,“居安思危”是不够的。 这些呼吁虽然指出了华人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却未能从根本上对症下药。华商如果只是采取某些收敛的态度,并不能消除族群之间的对立。而强调“弘扬中华民族主义”以对抗“原住民的民族主义”,更不是解决东南亚各国族群矛盾的出路。
在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内各民族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必然出现贫富分化,少数富裕华商与社会贫困阶层之间也必然存在利益的矛盾。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各国政府为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而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不应一概简单地视为“排华”行动。当然,这些政策的背后也可能带有原住民狭隘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成分,或某些原住民官员利用这些政策而排斥华人企业,或要挟华人企业以谋私利,这类现象的存在也是不可否认的。
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东南亚华裔公民比其他族裔在私营工商部门仍占有一定优势。因此,华商与其他族裔在互利基础上加强合作,帮助其他族裔的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共同目标,是东南亚华商的唯一出路,是化解东南亚国家原住民经济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正确途径。在世界各地,海外华人作为外来移民和少数族群,都会同样面对融入主流社会的问题,而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内的华人来说,真正融入主流社会更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东南亚华人作为一个少数族群,必须接受本土多数族群的文化,同时保留自身的传统文化,才有可能为建设各国现代化民族的共同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固然可以说,东南亚华人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文化,但华人必须入乡随俗,适应环境。如今,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文化显然已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文化。同时,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东南亚华人的商业根基则是在东南亚。只有立足于东南亚,首先为各自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才能得到本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华商企业的活动和发展是所在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商也只有随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
有些人用“华人经济”来概括东南亚华人的商业活动及其成就,并对“华人经济”的规模、实力以及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津津乐道,甚至鼓吹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华商聚集的地区共同建立“华人经济圈”。这种观点是把华商的经营活动孤立于东南亚各国国民经济之外,同时片面强调华人族群经商的才能和成就,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在任何国家内,都不可能存在独立于整个国民经济之外的“华人经济”或任何其他族群经济,而只可能有来自不同族群的资本或由不同族群经营的企业、厂商或公司。实际上,如今许多华商企业已包含其他族群拥有的资本,但仍可以某些指标(如华人资本所占比例,主要经营者是否为华人,等等)来认定这些企业属于华商企业。而众所周知,资本、企业、厂商、公司等只是经济活动的要素,但并不等同于经济。因此,“华人经济”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还应该指出的是,“华人经济”似乎只是中国大陆某些媒体和学者习惯使用的词语,而在国际学术界,相应的词语“Chinese economy” 则是专指“中国经济”,而不是“海外华人经济”。因此,宣扬“华人经济”的虚幻概念,只能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也给海外华商带来更大的困惑和面临更艰难的处境。
东盟的成立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开创了新的时代,大东盟的最终形成以及东盟10+3合作机制的实现,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东亚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当然也为东南亚华商走向海外提供了新的契机。东南亚华商应该审时度势,抓住这一机遇,主动搭上这一“顺风车”,加入到这一经济合作的框架内,并推动其他族群的企业一道,在推进东亚国家经济合作——当然包括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国家利益仍是国际经济合作出发点的情况下,东南亚华商自然要立足于各自国家的立场,维护并提升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谋求自身更大的发展。因此,在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东南亚华商既要努力实现东盟和中国的互利共赢,在东盟各国内又要实现国家和华商的互利共赢,而不可能脱离各自国家的立场,去追求所谓华商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存在超越国家利益之外的所谓海外华人的利益。
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