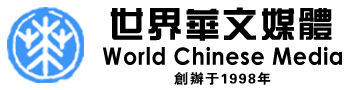十字路口的改变 ——读刘鹤达沃斯演讲的几点体会
十字路口的改变
——读刘鹤达沃斯演讲的几点体会
钱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一、信心指数与复利效应如何结合
二、中国改革现象学
三、十字路口的改变的时间之窗
四、重识小生产的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能力
五、什么是检验经济实践的价值标准?
刘鹤先生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主旨明确,就是通过展示“高质量繁荣稳定”的预期,提高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以分享中国消费、投资、进出口市场的“正面外溢效应”。
一、信心指数与复利效应如何结合
首先,这一主旨的贯彻落实,有经济学上的理论依据。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金・法马(Jin fama)、汉森(Lars Peter Hansen)和席勒(Robert J. Shiller),论证了资产价格既依赖波动风险和风险態度,也与非理性行为偏差和市场摩擦相关。因而仅靠财政激励政府是不够的,还需利用凯恩斯的第二个工具:生气、活力、血气甚至“无知近乎勇”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亦即信心,才能拯救世界经济。据此,席勒将巴隆(Barron)的信心指数(confident index)改造为Shiller指数估算。
基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判断,刘鹤先生演讲的“信心指数”(confident index)高,给世界超预期的底气足,这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需要,也是世界经济的需要。中国经济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个方向和定位完全正确——最让人眼睛一亮的是,过去两年中国做到了降能耗23%,简直是奇迹!
这里本着“成绩不讲跑不掉,问题不说不得了”的解决问题精神,说几点体会:
一、刘鹤的演讲前后两部分针对的对象不同:前面部分象是对下届政府和中国企业家说的,侧重国内实业界对发展的信心,后面部分象是对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甚至是对特朗普说的,侧重外界对中国经济特别是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大开放的预期。但是,前者有个权威性问题(权力并不等于权威,权威体现在执行力上),后者有个从“政治正确”的迷梦中醒悟过来的外部世界,买不买账的问题(特朗普达沃斯演讲有三处似针锋相对)。
二、信心指数并不等于“复利”效能:1、从需求侧(温的困境)到供给侧(朱的无奈),再到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问题一步步明朗,然在“权//控经济”边界内转圈圈,“三去一降一补”能不能保证优质?特别是降全社会成本和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肯定是大好事,但要受到政治惯性和体制性惰性的制约,甚至掣肘,如何克服?2、顶层设计需要底层驱动(企业、社会、公民)和中层动机(各级政府、基层组织和准政府性组织),如何落地?3、扭曲的市场经济如何在特朗普要求公平交易的“外部性”条件下加大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思路与对外开放的策略之间,如何恊调?
三、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来自中国自身,现在的基本情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渐进式改革的红利已经吃完,可用的谋略已经用尽,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代之而起的问题,是“一个矛盾、两大不足”。一个矛盾:是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冗官、冗兵、冗费已成难以承受之重(26个省市区吃财政补贴只是表象)。两大不足:一是动力学意义上,贪婪与套利思维,是动力,但非正道,缺乏安全感,非制度性反腐,导致懒政、外逃和观望,指标化的扶贫是输血而非造血(且无法杜绝“雁过拔毛”);二是恊和学(或恊同学)意义上,蛋糕做得再大,在既缺公平分配机制,又乏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平衡机制的情况下,环保举措也是“马后炮”,新城镇化已陷入形式主义,田园综合体和乡村振兴如何避免一刀切、同质化,“双创”之本在哪里?
指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但解决“一个矛盾,两大不足”的新问题,中国两千年积累的权谋和西方来的三百年科技经验都不足为凭,而非大智慧、大担当、大格局,无以应对。
我相信,对于真正的大政治家(“社会元勋”,2003)来说,这不是问题,而是改变现实书写历史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从依靠“精英”(圈子、政府),到依靠“草根”(公民、社会)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能力的共时性转型。
二、中国改革现象学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变法),从商鞅到王莽,从王安石到张居正,无论成败,从来是为了“官生”(钱宏,2011)!基于财政吃紧,官不聊生(民何以堪),倒逼出来的改革,总是由变通,至堵塞。
究其原因,也不外乎两个字:一个是“冗”,一个是“敛”。“冗敛思维”,始终是中国式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地。中国式革命思维,也是介乎“寡”与“均”两个字之间,但与改革不一样,“寡均思维”一旦导致改朝换代,总会出现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时期,最典型的案例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之治”、“咸平之治”、“洪武之治”,只是好景不长,给后人留下无限的记忆和憧憬。但不管怎样,“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自然经济条件下,却暗合了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所要求“政府、国民、社会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动力学与恊和学机制。所以,能不能不通过暴力革命而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是当代中国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时代课题。
平心而论,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与历史上的“冗敛思维”主导的改革,有很大区别,起码在解决“冗”“敛”的方式和范围上,与传统改革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引入外部性”“做大蛋糕”——一种经济开放套利思维主导的改革。
经济开放套利思维在理论层面的表现,侧重的是重量和数量的发展经济学。这种“硬道理”导向下的中国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只能为单纯的资本逐利效率(公平变成“兼顾”的对象)开便道,而所谓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更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为权控经济效益(法治变成“点缀”的配角)唱赞歌,这两种并非基于独立精神研究的中国特色主流经济学,看似在所谓“经济与政治”“公有制与私有制”“基础与上层建筑”上纠结不已,针尖对麦芒,其实在“官控资本”的意义上殊途同归——可谓相反相成了中国特色权力资本主义逻辑的滥觞。于是,有了“中国的奇迹”(林毅夫、蔡昉)与“奇迹的黄昏”(袁剑)、有了“市场”(吴敬琏)与“政府”(高尚全)、也有了“分蛋糕”(重庆)与“做大蛋糕”(广东),对于中国经济现况解释权重之争(边缘化的杨小凯、张维迎,及技术官员不在此列)。也有了基于公民自组织力与社会自组织力的“藏富于民”式“浙江模式”的异军突起。
无论学界、政界抑或国外怎么看,但从2002年至2008年中国的主政者心中是有数的,特别提出“科学发展观”那会儿,出现了一个改变套利思维的“转职能,调结构”的时间窗口。但遗憾的是,国际金融风暴骤起,“科学发展观”遭受猛烈冲击后,职能越转越泛,结构越调越偏,官生、民生公共资源的占比比重越来越向着官生倾斜(所谓“国进民退”只是一个表象),民生社会交易成本越来越高。
由于中国的过剩、库存、杠杆、社会成本、公共服务问题突出,而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有特别现实的针对性,也可以说抓住了“牛鼻子”,这是刘鹤超越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过人之处。
然而,撇开世界经济秩序重新洗牌的外部性因素,面临七十年政经夹击而日益“非自组织原子化社会”这一最大的“不充分”,面对四十年积累下来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这一最大的“不平衡”,已经到了再也不可能绕不过去“留给比我们更聪明的后人解决”的历史关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聪明阈值可能达成的效能,能承载起改变这个“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职能吗?
三、十字路口的改变的时间之窗
刘鹤先生在达沃斯演讲中特别提到:“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
这让我想到,最近比较活跃的楼继伟先生。在讲到“防范金融风险”时,楼继伟先生对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状况有四个判断。这四个判断,都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有关“混业经营”与“分业经营”及“混业监管”与“分业监管”的争议和实际措施直接相关。比如“非法融资”“产融结合”曾被严格限制,但现在,截至 2016 年末,涉足金融的大型控股产业集团就已达 53 家,且旗下包括银行、证券、信托、期货、公务基金、租赁、基金子公司、基金销售、第三方支付、小额贷款、典当等 11 个行业 252 家子公司和金控平台。
但在我看来,这种历史性重复,远不只是金融风险问题,也不只是滋生机会主义“生意观”,破坏实体经济秩序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中国特色权控资本体制所产生的社会导向-马太效应问题。这种“中国特色马太效应”,又是以资源高度集中为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和心理-物理条件的。只要我们当代中国人跳不出“经济与政治”“公有制与私有制”“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態纠结和既得利益羁绊,就不可能直面并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楼继伟有关金融市场的4个判断,依然只是表象描述。如上述53个“产融结合”混业经营的大型企业,赚钱太容易,积累了富可敌国的大量财富,实体行业没有竞争对手,又有政府扶持,实业部分不好也好,大量资金,进入金融市场,搞乱金融秩序,势所必然,防不胜防。结果,当然不只是造成可能的金融风险(如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和企业显/隐性债务等等),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社会商营环境和经济生態平衡,亦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良性循环”。
这样一来,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首战——防范金融风险,不仅远远超出是“混业监管”,还“分业监管”的范畴,而且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变的时间窗口中加以考量,也远远超出了“防范金融风险”的范畴。
也就是说,看似新瓶装旧酒,历史在重演,但我们的判断与因应之道,如果停留于简单的历史类比上,就永远走不出两千年“治乱循环”的维谷窠臼,进入不了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义)制度创新的轨道。
但是,正如刘鹤先生所言,当代中国确实处于一个“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我们当代中国人,站在这个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能看到历史再一次打开一个千载难逢的改变的时间之窗吗?
四、重识小生产的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能力
我相信,改变的时间之窗正在打开。这个改变,就是刘鹤先生讲的“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我们从“改变的时间之窗”望去,看到了怎样的景致呢?要落实到“三去一降一补”,就回到了中国内部更为纵深的事务。这就进入今年1号文件讲的“乡村振兴”的范畴了,正所谓“窗含西岭千秋雪”。
巧的是1号文件颁布前两天,我和温铁军、高俊才两位先生刚刚应邀到徐州市贾旺区江镇庄参加一个“乡村振兴座谈会”。19大后,习近平两度到徐州视察,再次强调,只有恢复青山绿水,才能使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
我们认为,落实习近平的指示,“恢复青山绿水”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即“一补”的范畴,而“变成金山银山”,则是如何释放当地人民和社会生命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能力的事。
这需要作一点历史反思。由于以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改革的认知偏颇,使农耕文明小生产长期背负着一个“落后”定义,必欲消灭而后快。殊不知,关涉城乡社区生活的小生产,是真正富有生命自组织内生性活力与外平衡能力的基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托底性源头,使得中国成为唯一没有终断文明史的国度。而建国后实施“以农养工”的抽水政策,后来以GDP增长率导向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用工业化方式发展农业养殖业,不仅“反哺农业”的政策无法落实,更全面破坏了中国的土质、水质、地质资源,对国民休养生息安身立命之身心灵健康产生了严重的扭曲,从而损伤了中国农耕文明亦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性活力。
如果说以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和农民税费负担为标志的“三农问题”确实反映了时代声音,但以“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村土地非农转用、农民离乡进城务工”为标榜的所谓“新三农问题”,却未必恰如其分!因为,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村土地非农转用,事关为资本、权力下乡开绿灯,也事关因地置宜,万不可一刀切,而农民离乡进城务工,几乎不等于农民直接融入城市,此三条,都涉及中国9亿乡村国民生产、生活的“进退之道,损益之术”。
作为一个躬耕田亩达十一年之久的思考者,我深知起码在“三山、六水、一分田”的中国南方,是本来孕育生物多样性与耕读传世文明发祥地。发展美国式的工业化规模农业,并不具备气候地理现实条件,且即使有技术上的可能,也没有如此趋同化的必要。请允许我冒昧地以为:只要是铁了心朝着这样三个目标之一或全部推进的政策导向——1、“农业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新老城镇化、产业政策与资本逐利三重需求下的所谓“劳动力自由流动”);2、“农村土地流转”(与所谓“私有制”“公有制”无关,却与资本下乡和权力操纵密切相关);3、“土地使用形態的市场化配置”(包括人为改变所谓“低效种植”“乡村旅游”“区域规划”“单色调经济”)——无论是发展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抑或新结构主义经济学,都是纸上谈兵的霸王硬上弓。这方面,远的教训有“三面红旗”后的“自然灾害”,近的即是目前整个乡村生活的衰落(这与美国城市空心化的社区生活破败,好有一比)。
经过国别比较和区域地域比较后,鉴于世界经济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的世纪钟摆”,导致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的间歇性周期发作,因而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倡导当下和未来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从“市场-政府两极形態”,升格为以“城乡社区经济”为托底的“市场-政府-社区三大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同时,超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部门划分,而伴之以“生態文明的成长与乡村生活的振兴”——为了缓解“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也许应当重新考虑退休官员“告老还乡”休养生息乡邻互惠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并且郑重出台鼓励吸引而非限制市民下乡做“新农人”的新政策——“让生产回归生活”!
五、什么是检验经济实践的价值标准?
《让生产回归生活!——共生经济学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我四年前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密歇根大学)上的演讲的题目。其中,我重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与朋友赵启正讨论的一个问题,即:工商文明的价值参量是GDP,那么生態文明也应当有一个相应的价值参量,而且,这个价值参量,同时也是检验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价值标准。
我们认为,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而能够适应这一历史大变局并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我们以为,就是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为基础的全球共生理念。全球共生理念,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将从“投资、内需、进出口”经济模式,转变为“生产、交换、生活”经济模式,也就是从重量、数量法则,向能量、质量法则的转变——“让生产回归生活”!
那么,什么是检验生产生活实践(如“三去一降一补”)的价值标准呢?
正如物理学已经从牛顿定律演化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玻尔量子力学,人类经济活动的物质总量进行衡量的准则,也应当从重量、数量准则,演化为能量、质量准则。工业化初期的重量法则,侧重于钢铁产量,中后期开始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增长,如今,到了生態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重视能量、质量法则,即从资本的增值、减值价值参量,转变为以能量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也就是生产生活质量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以完成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换,实现“一个总要求”——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今后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就,不是看GDP增长率,而是看共生经济学给出的“每单位资源生产效能贡献率”(含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看减轻地球背负、生態背负、社会背负为基础的GDE动態平衡率,所体现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与国民生活幸福度、尊严感。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给出的这个GDE价值参量,正是能量、质量法则的综合体现——既综合了美国兰德公司泰利斯等首创后工业化时代衡量国家实力方法、后续的“综合国力方程”(Klaus Knorr,1956)、“国家实力指数方程”(Clifford German,1960)、“非线性国力评价方程”(Wilhem Fucks,1965)、“国力评价方程”(Ray Cline,1975)和不丹国王的“国民幸福指数”、中国人大财经委的“民生指数”、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以及新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绿色GDP”的诸般努力——又回答了生態文明形態涉及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生態文明的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
这就是说,传统的指标和方法无法反映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条件下的国家和地区实力与国民生活与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效能,所以,摈弃重量、数量法则,使用能量、质量法则,评价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势所必然,人类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通信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善政良治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看那里的人民、国民、公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是否与其获得的幸福度和尊严感之间所呈现的反比例关系状况(H=G/T)。这也是衡量“一降一补”成效的价值尺度。
是故,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圣心连民心,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9亿农民或新农民,过去是,今天依然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生活的“托举哥”。中国执政党率先全球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农耕文明的历时性回归,也是对国民身心灵健康的修复;而贯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神的乡村振兴,在当代科技条件下,不仅可以促进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两大和解”,也可以促进工商文明“一、二、三产业”融合,将“市场-政府两极形態”,拓展为以“城乡社区经济”为托底的“市场-政府-社区三大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从而共时性地缓解“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这里主要是谈我读刘鹤先生达沃斯演讲的体会,有关“GDE价值参量”“三大经济形態”及相应条件的论述,就不多说了。
最后,我想说,刘鹤先生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得好,至少将为打开“改变的时间之窗”做出一个很好的铺垫,然而“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回到习近平“人民是我们力量源泉”(2012年12月25日新华社特稿),充分发挥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常態上来。
为此,我们需要一种作为习近平新时代精神的精华与生態文明活的灵魂,涵盖动力学与恊和学效能的追寻可能世界的新哲学!
这些粗浅感想,未知是否合适,敬请方家指正。
2018年2月6日于复旦大学北区望道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