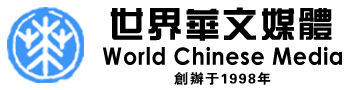主流媒体的影响与二十一世纪华文媒体的前景
主讲:俞力工 (奥地利《奥中资讯网》主编)
华文媒体的道德
八、九十年代之交,罗马尼亚动荡不堪。有一度全球媒体同时传播着从该国发布的几个镜头,即几具刚由地下挖出来的尸体赤裸裸地展现在屏幕上,死者的年龄不等,而每具尸体胸腹上经过缝合的伤口则清晰可见;其旁白则是,“这些人都是国家安全人员暴行之下的牺牲者”。数星期后,共产政权崩溃,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也遭枪决。突然间,个别媒体又传出“那些尸体其实是经某医院解剖之后才埋葬的病亡者”。
消息来源地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刻意传播错误消息的例子在全世界多得不胜枚举,之所以提及此事件,主要是因为欧洲新闻界与学术界事后对该事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即为何全球媒体明明知道受骗上当之后,多不愿继续报导和加以纠正?最后,大家得到的一致结论是,大多媒体将错就错的原因在于,散布该错误消息可以达到反共的目的。
有选择性地报导部分事实,从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类似例子,甚至也发生在联合国最近所发布的数据上。以科索沃的动乱为例,在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轰炸之前,科索沃地区的塞尔维亚族难民的人数其实远远超过阿尔巴尼亚族的难民人数,但是,3万多塞族难民逃亡的事实,联合国直到轰炸结束之后才发表。除此之外,即便该数据经发表之后绝大多数媒体也置之不理。至于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之后,相继有90%的塞族居民和吉卜赛居民遭到阿尔巴尼亚族的驱赶的消息更是受到西方媒体普遍的压制。究其原因,也不外是担心,事实真相一旦揭露,主流社会及主流媒体的双重标准就曝露无遗。
谈及双重标准,如果拿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与土耳其库尔德族的处境作一对比,拿六、四天安门事件与二十年来东帝汶牺牲了四分之一人口的事实作一对比,我们应当意识到,冷战时期的反共思维实际上仍旧起着主导作用,当前在这块遮羞布的掩饰下,真正的人权、尊严、正义不断受到严重的摧残。有鉴于此,读者群几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华文媒体,实有必要拿出起码的职业道德,挺身而出,为各种不同性质的不公平、不合理事件伸张正义。
华文媒体的智慧
本人今年六月途径台湾桃园机场时,在候机室的电视前足足看了3个小时的CNN新闻报导。当时的消息其实只有一条,即美国前总统甘柰迪的儿子下落不明。本人原以为这种小题大作不过是CNN的独家把戏,事后却发现无论是台湾本地的电视台、欧洲的电视台,甚至香港的一些官办报纸都把该事件作为头条消息大肆报导。如果我们联想到克林顿的绯闻、辛普森杀人案、戴安娜之死等等,我们柰不住地要问,这些无关紧要,甚至荒谬绝伦的事件究竟与我们何干?!难道世界上就没有更加值得一提的大事儿了吗?难道我们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让这些消息入侵我们的客厅、卧室,以致于让我们的孩子觉得甘柰迪与戴安娜比爸爸、妈妈还亲吗?当华文媒体的负责人不假思索地传播这些消息之时,难道就没意识到,主流媒体对新闻的取舍完全是种自觉的行为吗?!我认为,许多华文媒体之如此大意,如此把别人的尾巴当作自己的头,完全是对华人的智慧进行无边的羞辱。有鉴于此,我在此呼吁华文媒体发挥起码的智慧,摆脱主流媒体所限定的范围,多向五分之一的人口报导一些他们真正关心的消息。
自古以来,有商品即有宣传与广告,但是把商品当作文化,文化当作商品一并推销,还是近几十年的新颖手法。举例说,要表现男人的冷酷气概,便必须点燃一只万宝罗香烟;要模仿出水芙蓉,就必须手持一杯可乐加冰块;要作新人类,要获得点现代参与感,便得进出卖当劳;要想占后现代之先机,必须拿出壮士断臂的勇气脱离传统、摒弃历史,然后大胆地把风牛马不相及的概念、辞藻、标签组合起来。于是乎,目前所谓的主流文化,实际上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标签组合而成的百衲图,标签之间不需要有任何的有机关系,不需要任何的逻辑关系和合理性。所谓的现代社会,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一堆堆的商品,同时又是一片片杂乱无章的文化。然而无可否认,这所有的标签、概念、商品、文化又都是透过我们的媒体吸收进来和释放出去。正是我们自己的媒体,毫不自觉地又勤勤恳恳地充当着西方文化的媒介。
当前,在国内,我们不时可从六、七岁的孩童口中听到“我只爱喝可口可乐!”此时,我们柰不住地要问,这么丁点大的孩子怎么会产生这种观念?难道少说也有四千年饮食文化的中国,不过遭遇到几个可口可乐的广告就一筹莫展了么?!难道我们的饮食文化也像民族音乐、服装、绘画、戏曲、手工艺一样,在西方大众文化之前就只能自惭形秽吗?!
难道我们的媒体在“全球化”的旗帜之下发挥传播作用之时就只能让自己的文化靠边站吗?!我担心,再过十年、二十年,即便那时中国的国防力量、物资力量强大了,文化与人格却已严重地歪曲和萎缩。在这方面,只消观察某些石油输出国家的权贵阶层的苍白与失落,便知道脑满肠肥的奴隶,其实是更加可悲的奴隶。或许有人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落问题,但是只要一旦国家综合实力提高,便会自然而然地调整自己的定位。我认为,情况即便如此,我们的文化界、新闻界似乎不一定要等到自己的文化奄奄一息之后再设法起死回生,不一定要在扬眉吐气之前先经历一段作奴隶的痛苦。我们华夏民族应当具备现代化而不受殖民化的能力与智慧,我们的华夏文化应当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深厚土壤。有鉴于此,我在此呼吁华文媒体在发挥传媒作用时,也能够考虑到发扬华夏文化的职责。
综合上述的意见,无论是发扬道德、智慧或文化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华文媒体所存在的两个瓶颈:一是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的“由外语人材主管外事工作”的落后现象。具体而言,在华人社会,无论是外交、外贸、国际新闻或文化交流领域,绝大多数的工作人员都是外语人材。而西方,则主要是法律、政治、经济、教育或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方面的专材。以外交官为例,不难理解,在过渡时期由外语人材从事外交工作,可能是个别无选择的办法,但其不妥当之处,恰好就像是要求学习汉学的文学士去主管内政。国际新闻方面也也是如此,懂得英语并不一定懂得英美社会的政治、经济、贸易和社会问题。贸然要求他们从事这些方面的新闻工作,也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最近,在北约结束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之后,台湾《中国时报》的一位女记者也凑热闹地跑到科索沃去采访消息。当她听说科索沃的
吉卜赛人受到阿尔巴尼亚族的迫害之后,竟然说吉卜赛人是“自作孽,不可活”。之所以闹出这种笑话(其实是悲剧中的悲剧),就因为这位仅懂得点外语的新闻工作人员与编辑组审校人员对西方的种族纠纷和传统文化一窍不通。当我看到这条报导时,真是难过之极,同时也深深地感到,这种畸形现象如果不加以纠正,华人社会的涉外工作质量就不会有所提高。
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瓶颈就是当前各大媒体所存在的“由新闻记者主管编辑部、导播部事务的现象”。由于记者的主要工作经验在于争取时效写报导、发消息,因此一旦参与编辑工作就会习惯性地把过去的工作经验规定为编辑方针。举例而言,任何编辑部均可期待新闻记者就有关法轮功问题作一个及时且详细的报导,但却不能要求记者对同一问题提出一篇有深度的分析与评论。因此,在多数编辑部、导播部由新闻记者把关和盲目追求时效的情况下,一些有分量、有深度的社会分析与评论就必然要让位于时事综合报导;久而久之,时事报导也就取代了评论的地位。换言之,该状况必然会把记者提升为“评论家”,而评论家为了增加稿件的登载率也就必须得向新闻报导看齐。
与西方的媒体加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华文媒体的评论、分析极端贫困,因此就永远不可能摆脱地方报纸、地方电台的地位,永远不可能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更用不着说去同国际性大报、国际性电台、电视台竞争。如果进一步观察,我们又会发现,上述两个瓶颈实际上是一个铜版的两面,其问题症结就在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着歧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现象。因此只要华人社会继续忽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就永远无法培养充分的专业人材,也就永远无法向各种涉外机构、编辑部、导播部提供称职的工作人选。要想解决这个迫切问题,我们一方面期待媒体单位认识到自己的短缺,从而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必要的调整;另一方面则必须要求各个国家当局即刻提高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教育的重视与投资。唯有如此,唯有在华人社会的知识界、文化界明确自己的地位,肯定自身文化的价值,和明确辨别外来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情况下,华文媒体才能够在二十一世纪大放光彩。

1999年10月11日,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成立暨 “ 走向21世纪的中文媒体研讨会年会”主题发言